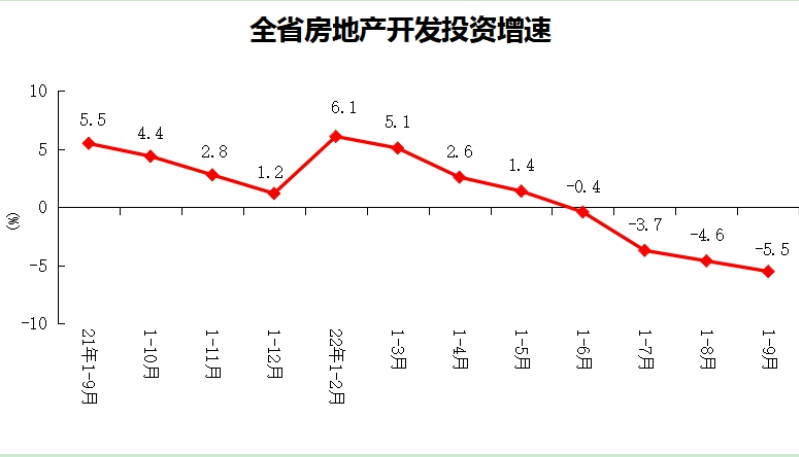大象新聞記者 申子仲
 (資料圖)
(資料圖)
11月22日,節氣步入小雪。剛剛經過一場陰冷冬雨的浸潤,清晨的鄭州,大街小巷較以往顯得愈發通透。作為省會面積最大的老舊小區——汝河小區的北門口,漸漸熱鬧起來。肅穆的帳篷、嚴格的“大白”、緊閉的柵欄、呱噪的小喇叭起伏著安全提醒……顯然,眼下的汝河小區仍在與新冠病毒做著殊死搏斗。
這是最后的斗爭!
緊張的“前敵司令部”,此起彼伏的電話鈴聲
汝河小區建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樓體為五、六、七層高的老式“火柴盒”建筑,多達104幢、299個單元。住有3600戶6000多人。占地300畝,東至桐柏路、西達伏牛路、南臨淮河路、北抵汝河路。是鄭州市最大的老舊小區。
因“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汝河小區同時也是一個社區。社區的抗疫指揮部,就設在離北門不遠的黨群服務中心內。
11月22日上午10點多,大象新聞記者走進黨群服務中心的第一印象,就是這里的場景,像極了戰爭影視劇里的“前敵司令部”——
門口和大廳里堆積著各類防疫物資包裝紙箱,中央的辦公桌上,堆滿雜七雜八的各類用品和文件。10多間辦公室里,場景與大廳相仿。辦公人員來回穿梭,相互照面招呼著各項具體工作。隨處是此起彼伏的語言交流和電話鈴聲,使得本就不太寬敞的區域,顯得格外擁擠,甚至凌亂,而即便是在如此嘈雜的環境下,竟然還有一位“大白”趴在辦公桌上呼呼大睡。
記者問“司令員”劉繼紅,趴著睡覺的是誰?
“裹得這么嚴實,我也說不上是誰。只知道是咱小區的志愿者,估計是太累了。”劉繼紅吩咐同事們別叫醒他,便把記者讓進了辦公室。
“無論哪一支隊伍,都少不了志愿者”
狹窄的辦公室堆放著各類紙箱,沙發上鋪著一床被褥,“劉司令”已在這里住了40多天,從沒回過家。
劉繼紅一米八的高個子,略顯女性化的名字,倒是和他消瘦的身材有點搭。
說來也是機緣巧合,48歲的劉繼紅原在汝河路街道辦事處城管科工作,2019年底,受命來到汝河小區社區“掌門”。本來,上級指望著他來“啃”老舊小區改造這塊硬骨頭。不料上任沒幾天,便趕上了2020年的第一撥疫情。
3年來的一線抗疫磨礪,已經讓臨場經驗豐富的“劉司令員”指揮若定。他一邊接著電話指揮“作戰”,一邊介紹著一個多月來的戰況:
10月9日,小區發現首個病例,社區防疫指揮部臨時黨支部隨即成立;10月11日晚,汝河小區按照統一部署正式整體封控;從這一天開始,小區原有的5個大門,僅留下東側和北側兩個大門可供出入,其中北門用于一線工作人員出入,東門用于物資保供和人員轉運。
“我們社區有十多名工作人員,市農委機關下沉支援30人,辦事處科室和派出所支援10多人,小區物業20多人,樓長及志愿者近百人,除了核酸醫務人員,常態一線抗疫隊伍保持在180人左右。”劉繼紅說,三年疫情反復,提升了基層的黨建引領水準和突發應變能力,隊伍集結迅速分工明細,為這次動態清零、精準防控打下了堅實基礎。
有了機關下沉人員的支援和志愿者的加盟,近200人的大部隊,緊隨疫情形勢分劃成值崗巡視、物資保供、保潔消殺、核酸檢測、追陽轉運幾個支隊。其中機關下沉人員主要負責值崗巡視;物業主要承擔保供、配送、衛生保潔及垃圾清理;外聘消毒公司主要包攬小區全域消殺;相對較為危險的核酸檢測、追陽及重點人員轉運等工作,社區責無旁貸。“無論哪一支隊伍,都少不了志愿者。”
追陽志愿者的家人也陽了,“非要圖點啥嗎”
作為有年頭的老舊小區,汝河小區居民人員構成復雜,其中老年人、外來租房戶占比60%以上,老職工居多,社會關系繁雜,管理難度相當大,相應的疫情形勢也頗為嚴峻。統計數據顯示,截止11月22日累計確診的陽性病例達到302個,先后散布在90多個單元門洞。
就是在如此危難的處境下,汝河小區依舊涌現出一大批敢做敢為的志愿者。
42歲的齊海濤是59號樓居民,平時主要做鋼架結構的建筑生意。小區防疫戰剛一打響,作為小區抗疫的老志愿者,他再次義無反顧報名“參軍”。齊海濤家有一兒一女,大女兒上初中有網課,和媽媽一起呆在家里。小兒子才5歲,正是調皮搗蛋的時候。為了減輕妻子的負擔,也不影響女兒學習,齊海濤就效仿反清復明的大俠洪熙官,帶著兒子“行俠仗義”。由于此次疫情來勢洶洶,安全起見,他干脆在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會議室里安了一張行軍床,和兒子一同起居。每天早上他把孩子安頓到社區圖書室,便獨自斗志昂揚殺向戰場。
和許多志愿者一樣,齊海濤也是身兼數職,除了核酸檢測信息采集、落實重點人員管控、接送醫務人員外,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最危險的“追陽”。擔心兒子的安全,齊海濤也是小心翼翼,每天下了戰場,都要謹慎清理消毒。
令齊海濤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家里同單元樓上出現了陽性病例,10月30日夜間,社區接到了新的“追陽”指令,當他拿到名單的那一刻,發現妻子和女兒名字赫然在列,短暫的驚愕后他毅然穿戴好防護服,帶著醫務人員敲開自己的家門,最終也不得不接受現實,妻子和女兒也被確認感染。
“那天是我送老婆和女兒上的轉運車,難受極了,真是心如刀割。”回憶起那天的情景,齊海濤至今還眼圈泛紅。
家人的感染,沒有讓這位俠骨柔腸的志愿者退縮,反而更堅定了心頭的責任。時刻在一線沖鋒的他,從此多了一份牽掛,每天微信視頻打探家人的健康。11月15日和19日,齊海濤的妻子和女兒先后治愈歸家,這位鐵打的漢子也顯露出了久違的欣慰。
直到記者蹲點采訪時,齊海濤依舊帶著5歲大的兒子奮戰在戰地最前沿。記者問這位生意人“這樣做圖的啥?”
齊海濤摸摸下巴,笑著反問:“非要圖點啥嗎?”
倒貼錢的蔬菜包和帳篷,“第一突擊隊”的戰術
“有段時間運輸車輛緊張,齊海濤就開著自己的私家車,每天接送做核酸檢測的醫務人員。”劉繼紅動容地說,不要報酬還開車倒貼油費,“咱的志愿者,真是無私奉獻,太無私了。就是人們說的‘心里只有別人,唯獨沒有自己’。”
同樣倒貼錢的,還有管理汝河小區的物業公司。
億眾物業公司是2018年5月入駐接管的,運營一直處于虧損狀態。盡管如此,疫情期間,本就沒有“余糧”的物業還是硬氣了一把,從牙縫里摳出20000多元錢來,一次性定制了3000多份30000多斤蔬菜,在形勢最嚴峻、居民生活物資最短缺的時刻,分發到全小區每家每戶。
一直倒貼錢的,還有對口下沉支援的鄭州市農業農村工作委員會的30名工作人員。因為響應“戰疫”最早,這支隊伍還有一個響亮的名字——“第一突擊隊”。
也是從疫情阻擊戰打響第一天開始,“第一突擊隊”的帳篷便陸陸續續扎進“營地”。隨著精準防控措施的實施,30多個帳篷,對應扎在了小區的33個高風險樓洞單元口。這些帳篷,都是鄭州市農委無條件自費支持的。
掛帥“第一突擊隊”的,是農委農產品質量檢測中心主任呂紅偉。
這位50歲的干部,像極了戰爭片里部隊政委的角色,他向記者介紹說,“第一突擊隊”的戰術就是“想辦法、定方案、制措施、明紀律、嚴要求、親歷為”,針對各種問題,要求突擊隊員分包到樓、細化到事、責任到人,“自下沉以來,勸阻人員1400人次,維持核酸秩序25000人次,裝運蔬菜30000多斤、配送500余次。”
三班倒值崗巡視,是“第一突擊隊"的最基本工作,記者從郭智廣、袁小偉、王建濤、龔志軍、申占斌等幾位下沉隊員的手機里發現一組數據。他們每天的步數,最多的22000步,最少的也在8000多步。
睡得最少吃的最晚,離家700米竟40多天沒回家
中午的時候,劉繼紅客氣著挽留呂紅偉吃飯,呂紅偉擺擺手,起身告辭。
目送呂紅偉走遠,劉繼紅有點不好意思地對記者說,按說這些下沉單位一線工作人員的伙食,也是應該由社區負責的,但農委為了減輕社區的負擔,自個給解決了。
忙碌著給大家分盒飯的,是社區的副書記孫雪君。
自從上午記者踏進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的大門,就沒見她閑過。
30多歲的孫雪君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是社區工作人員公認的“睡得最少的人”之一。這次抗疫,她主要負責每天的核酸檢測工作安排和各類臺賬信息統計。“核酸檢測劃片分組,是最麻煩的事。”孫雪君說,因為每次到小區的醫務人員都是臨時指派的,人數不定、人員不定,且因中途變化,常常臨時更替,有時候半夜兩三點才能敲定。她幾乎天天6點左右到社區,開始根據幾個小時前確定的醫務力量和檢測方式分配信息員和劃片點位。每天都是從天黑忙到天黑。
孫雪君的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一個上幼兒園。她家住在淮河路,也就是汝河小區的南側,與她上班的所在,直線距離700多米,步行10多分鐘,騎車兩三分鐘。
就是這么短的距離,疫情防控以來,這位女士硬是沒回過家。
記者也在社區“蹭”了一頓盒飯。
大伙埋頭干飯的時候,劉繼紅始終沒動筷子,記者偷偷問社區工作人員楊青,“司令”為啥不急著吃飯?
楊青說他就這樣,每次都是等別人吃完了,他才吃。
記者玩笑說,怨不得那么瘦。
“最危險的活兒,肯定我先上”
因為剛下過雨,小區里不少帳篷內有積水,加上天氣陰冷,擔心電源安全,汝河路辦事處下派來的宣傳委員李丙乾和“第一突擊隊”的呂紅偉一同去各處帳篷巡視情況,順便帶上記者。
路上談起劉繼紅,李丙乾對記者說,“別看他瘦,可有勁兒。”
呂紅偉和李丙乾講了個故事:汝河小區一幢居民樓3單元4樓住在一家三口,其中老太太85歲,老爺子82歲,全都癱瘓在床10多年,疫情期間,只有60多歲的兒子在家照顧。10月18日,一家人被確診陽性。精準防控以來,老齡確診病例的救治,都是社區通過危疾重癥病人途徑,聯系疾控120及時送往指定醫院救治。
當天聯系好120,劉繼紅便提前下手,自個穿好防護服上了樓。先是給兩位老人穿防護服,因為老人的身體癱軟,四肢不會活動,而劉繼紅自己也穿著“大白”,手腳頗為不便。他咬著牙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和老人的兒子前前后后忙活了近一個鐘頭,才幫兩位老人套好防護服。
120急救車趕到后,擔心樓道過窄樓梯偏陡,而老人不能配合,加上他們的兒子也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出于安全考慮,也擔心耽誤過多時間,劉繼紅索性豁出去了,兩回兩趟,將老人背下樓送上車。
送走老人回到社區消完毒,脫下防護服的劉繼紅,仍是滿頭滿身汗水未銷,腿肚子只轉筋。有同事打趣問他出了幾兩汗,劉繼紅玩笑說“至少兩斤”。
經住院治療,被劉繼紅背下樓的老人,于11月11日出院返家。這次,劉繼紅沒敢逞強,他提前找來了輪椅,和志愿者一起,將老人抬回了家。
“最危險的活兒,肯定得社區上。社區里誰先上?我是頭兒,肯定是我先上。”劉繼紅后來對記者說,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邏輯,“誰讓你是頭兒呢”。
“病毒無情,中原有愛”
由于精準防控措施得力,汝河小區高風險單元由最高峰期間的33個,迅速銳減,只剩下5個。而整個汝河小區也降級為低風險區域。
就在記者采訪的當天中午,疾控部門又傳來利好信息:73號樓、18號樓2單元、82號樓4單元符合解封條件,將于23日降低風險等級。
剛吃完午飯的劉繼紅馬上將這個好消息電話通知給呂紅偉,呂紅偉也是大喜過望,說下午就組織召開黨支部會議,研究這三個單元的解封細節。
雨過天未晴,午后的汝河小區安靜了許多。在18號樓2單元樓洞口前,大白還堅守在哇涼哇涼的帳篷里,短短的警戒線后邊,樓洞口遮雨沿上方,懸著醒目的“高風險單元”牌子。下面則是張貼得規規矩矩的“防控公示欄”,包括消毒處置、下沉人員執勤表、每兩個小時一次的巡查記錄等表格,以及《致轄區居民的一封信》《致轄區隔離轉運群眾的一封信》《致居家隔離朋友們的一封信》《居家隔離觀察事項告知書》等等,每一組數據,每一句話語,無不滲透著防疫工作人員的辛勤汗水和良苦用心。
“病毒無情,中原有愛”“靜是力量,宅是貢獻”“沒有邁不過的坎,沒有越不過的山”“疏解好壓力,調整好心態,蓄養好身體”“以靜制動,盡早清零”“咬緊牙關,同時間賽跑,同病毒較量,一鼓作氣奪取最后勝利”……提氣的金句,字里行間比比皆是。
真想安安生生看場球賽
下午的黨支部會議小范圍召開,因為有了前期的解封經驗,73號樓、18號樓2單元、82號樓4單元三個待降低風險單元的具體解封事項及下沉值守人員分班調整很快敲定。
組織會議的是呂紅偉,按照上級黨組織的規定,原先的社區疫情防控臨時黨支部新近改組,書記劉繼紅“讓賢”,由副縣級下沉干部呂紅偉任臨時黨支部書記,李丙乾任副書記,劉繼紅和其他4名黨員干部任委員。
呂紅偉有著27年黨齡,李丙乾黨齡19年,劉繼紅雖說黨齡最短,卻是當年武漢疫情爆發期間,因一線防疫工作突出火線入黨的。
黨旗飄起來、黨徽亮起來、黨員動起來,黨建引領汝河小區社區一個多月的連續奮戰,阻擊戰已經轉為殲滅戰,捷報頻傳,勝利在望。
當晚23時許,記者致電劉繼紅,電話被掛。還以為他已經休息,便不再打擾。不料23時30分許,劉繼紅回了語音短信,說剛才在開視頻會議,商量次日核酸檢測的事項,所以沒來得及接電話,“敬請諒解”,還說自己的手機24小時開機候命,隨時都能打通。
23日0時許,世界杯墨西哥對波蘭的比賽已經開始電視直播,記者再次致電劉繼紅,他正在小區里巡視,忙活著三個待降低風險等級單元解封的事。
記者問他一天能保證多長時間的睡眠,劉繼紅說大概也就四個多小時,就這也沒睡過囫圇覺。
記者又問他,等疫情過去了,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那邊的劉繼紅似乎是聽到了電視機里傳來的動靜,打著哈欠說:“我最想跟你一樣,安安生生看一場球,我可是鐵桿球迷啊。”
-
環球新動態:百度在線營銷收入環比回升 智能駕駛累計訂單將達114億元
頭條 22-11-23
-
全球最資訊丨總投資1.01萬億元,安徽省下達1566個重點項目投資計劃
頭條 22-11-23
-
中國銀行與萬科簽署戰略合作提供不超過1000億元授信額度
頭條 22-11-23
-
最新消息:農業銀行與五家房企簽署銀企戰略合作協議
頭條 22-11-23
-
又有百億私募自購!自有資金押注超60億,私募自購潮涌現?年內已有15家自購
頭條 22-11-23
-
8801.9億元!河南前三季度商品、服務類電子商務交易額位居全國11位
頭條 22-11-23
-
世界快訊:國家發改委價格成本調查中心赴全國煤炭交易中心開展煤炭流通成本調研
頭條 22-11-23
-
天天熱門:交通銀行向萬科集團、美的置業提供授信意向額度超千億元
頭條 22-11-23
-
深圳發布首貸戶貼息實施細則 單戶企業貼息金額最高20萬元
頭條 22-11-23
-
前沿資訊!多氟多:鈉離子電池已有小批量成品下線
頭條 22-11-23
-
世界今頭條!河南昨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15例、本土無癥狀感染者736例
頭條 22-11-23
-
當前消息!中證協發布證券公司數字化轉型報告,信息技術投入338.2億元
頭條 22-11-23
-
今日關注:鄭州市惠濟區新增3個高風險區,8個降為低風險區
頭條 22-11-23
-
鄭州市金水區新增11處高風險區
頭條 22-11-23
-
環球觀察:鶴壁淇濱區公布3例無癥狀感染者活動軌跡
頭條 22-11-23
-
【全球播資訊】國家衛健委:昨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2641例、本土無癥狀感染者26242例
頭條 22-11-23
-
鄭州市鄭東新區13畝產業用地掛牌出讓,起始價為1.17億元
頭條 22-11-23
-
滾動:A股邁上“5000家”科創底色日漸濃
頭條 22-11-23
-
當前觀點:隔夜歐美·11月23日
頭條 22-11-23
-
河南省農信社改革方案已獲銀保監會批復 將組建河南農商聯合銀行
頭條 22-11-23
-
天天快播: 立方風控鳥·早報(11月23日)
頭條 22-11-23
-
天天熱點評!中牟新鄭新密滎陽登封5縣(市)開展3天集中核酸篩查
頭條 22-11-23
-
頭條焦點:鄭州高新區通告:調整部分區域風險等級
頭條 22-11-23
-
鄭州市二七區通告:32個區域劃為高風險區
頭條 22-11-23
-
天天微速訊:四方達采購4300斤蔬菜,助力中牟農產品促銷|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全程直擊!中牟2萬斤促銷蔬菜直送鄭州市民餐桌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環球看點!安陽市政府:涉事企業法人代表已被公安部門控制
頭條 22-11-22
-
熱議:登封市發布通告:調整部分區域風險等級
頭條 22-11-22
-
全球觀天下!光力科技擬2.08億元轉讓全資子公司股權
頭條 22-11-22
-
【天天播資訊】重磅!證監會新一輪上市公司提質方案已定!
頭條 22-11-22
-
全球微動態丨“我要采購”!助力蔬菜找出路,這場連麥引關注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每日播報!滎陽市通告:11月23日、24日、25日開展集中核酸篩查
頭條 22-11-22
-
秋樂種業北交所IPO本周五申購,發行價6元/股
頭條 22-11-22
-
環球快報:榮耀發布MagicOS7.0 未來或兼容iOS及鴻蒙
頭條 22-11-22
-
天天熱訊:百度Q3營收、凈利潤雙向增長,汽車制造商對其自動駕駛方案需求增長
頭條 22-11-22
-
焦點觀察:立方風控鳥·晚報(11月22日)
頭條 22-11-22
-
天天簡訊:中牟洪潤瓜菜合作社發出邀請:七成蔬菜急尋銷路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大河農業批量采購全省急銷蔬菜,向各類企事業單位食堂輸送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天天即時:滑縣3000萬斤芹菜待售!財立方直播連麥后已有企業對接菜農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王凱在安陽指揮“11·21”火災事故處置工作
頭條 22-11-22
-
環球關注:鄭州富士康:園區餐廳11月23日起全面恢復堂食
頭條 22-11-22
-
河南供銷系統合力助農銷售蔬菜上千噸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世界快看:向菜農伸出援手!河南公益助農蔬菜愛心集裝箱等你認購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環球視點!前沿觀察:從飲品到文化,洞悉中國咖啡市場的發展之路
頭條 22-11-22
-
【環球快播報】鄭州市新增1例死亡病例情況通報
頭條 22-11-22
-
精選!中原再擔保集團全員響應+餐廳采購,2000斤助農蔬菜已端上餐桌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代號7天連鎖便利店成立助農專項小組,已采購20多噸愛心菜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2
-
中國平煤神馬控股集團:擬最高增持1.88億元神馬股份股票
頭條 22-11-22
-
創投日報(11月22日)
頭條 22-11-22
-
中國銀行海南省分行行長林振閩任職資格獲批
頭條 22-11-22
-
河南79家小貸公司已退出試點,但未注銷登記或辦理名稱經營范圍變更 | 名單
頭條 22-11-22
-
全球觀察:全文發布!銀保監會明確保險公司開展個人養老金業務資質條件
頭條 22-11-22
-
消息!鄭州上街區“云端”課堂有趣又有料
頭條 22-11-22
-
護航萬邦市場,他們風雨無阻
頭條 22-11-22
-
當前消息!鄭州慈善救助系列活動確保困難群眾溫暖過冬
頭條 22-11-22

- 精選!蹲點日記⑤ | 這是最后的斗爭!鄭2022-11-23
- 今日熱議:銀杏插花作品 寄寓美好祝愿2022-11-23
- 全球消息!世界杯吉祥物“拉伊卜”被搶注,2022-11-23
- 快資訊:歐美或將在 2030 前擺脫對中國電2022-11-23
- 1 小時 1 元“想玩多久玩多久”,防沉迷2022-11-23
- 全球快看:偽球迷裝 X 手冊丨奇奇奇奇奇2022-11-23
- 環球新消息丨航天新征程 | 逐夢星辰大海2022-11-23
- 最新快訊!金融街論壇首設文化分論壇釋放哪2022-11-23
- 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棕櫚股份助力夯實鄉村2022-11-23
- 武漢三鎮青年球員陽敏杰前往德甲球隊斯圖加2022-11-23
- 對話世界杯吉祥物玩偶“拉伊卜”二次開發團2022-11-23
- 省應急廳胡方敏一行蒞臨泌陽督導檢查 非煤2022-11-23
- 環球新動態:百度在線營銷收入環比回升 2022-11-23
- 世界百事通!女子討要一點豬油,肉鋪老板連2022-11-23
- 全球最資訊丨總投資1.01萬億元,安徽省下達2022-11-23
- 羅山:持續優化“獲得用水”營商環境2022-11-23
- 中國銀行與萬科簽署戰略合作提供不超過10002022-11-23
- 環球最資訊丨泌陽縣應急管理局組織召開行政2022-11-23
- 每日熱議!湖北試行統一醫保定點醫藥機構協2022-11-23
- 最新消息:農業銀行與五家房企簽署銀企戰略2022-11-23
- 又有百億私募自購!自有資金押注超60億,私2022-11-23
- 天天最新:泌陽縣應急管理局開展2022年度行2022-11-23
- 蔡甸九真山水杉紅了,還有這些景點可打卡2022-11-23
- 動態焦點:羅山:實施縣城分區計量 為供水2022-11-23
- 萬民商城:助力三十萬家小微企業,打造安全2022-11-23
- 蘇魯豫皖四省舉行聯防聯控桌面推演暨衛生應2022-11-23
- 遇見初冬 這座城“鄭”在想你2022-11-23
- 熱點評!“噓寒問暖·大象幫”? | 熱源2022-11-23
- 全球熱文:省商務廳多措并舉開展蔬菜促銷助2022-11-23
- 每日播報!諸神之戰|“奇異博士”諾伊爾:2022-11-23
精彩推薦
閱讀排行
- 精選!蹲點日記⑤ | 這是最后的斗爭!鄭州最大老舊小區的抗疫“決戰”
- 蘇魯豫皖四省舉行聯防聯控桌面推演暨衛生應急工作視頻會商
- 遇見初冬 這座城“鄭”在想你
- 熱點評!“噓寒問暖·大象幫”? | 熱源不足群眾有氣,鄭州如何答好這道民生考題?
- 全球熱文:省商務廳多措并舉開展蔬菜促銷助農工作
- 每日播報!諸神之戰|“奇異博士”諾伊爾:不畏挑戰的彪悍人生
- 天天速看:“卡”車來了|梅西首秀破門難救主 沙特2:1爆冷擊敗阿根廷
- “卡”車來了|阿根廷首戰沙特失利 梅西慌得一批
- 環球微速訊:河南住房公積金網上業務量持續提高 前三季度同比增長3.25%
- 天天看熱訊:中牟新鄭新密滎陽登封5縣(市)開展3天集中核酸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