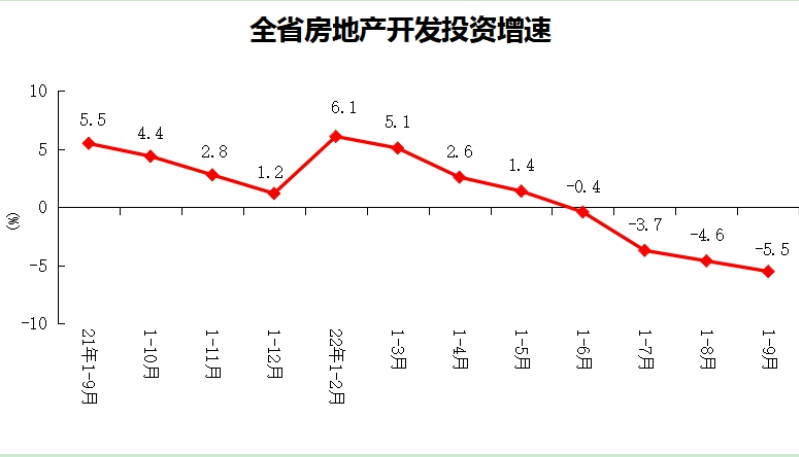大象新聞記者 李昌
作為陪診師,黃笑迪曾有過一段至今難忘的經歷:她曾陪一名中年大叔患者,瞞著家人,轉診到北京手術。她感嘆:“這個工作,讓原本陌生的兩個人相依為命!”
近日,一則廣西舞蹈老師改行當陪診師月入過萬的新聞登上熱搜,讓陪診師這個新興行業進入了人們的視線。陪診師的工作究竟如何進行?他們的月收入真有那么高嗎?他們有什么體會……在接受大象新聞記者采訪時,鄭州前資深陪診師黃笑迪一一講述自己的感受。
 (相關資料圖)
(相關資料圖)
“90后”女孩黃笑迪坦言,這段特殊經歷讓她見證悲歡離合,人情冷暖,以至于決定改行,但是能夠陪同別人熬過一段看病求醫的苦日子,內心收獲的是平靜、美好。
圖源:視覺中國
入行:“久病成醫”,意外成了陪診師
“我叫黃笑迪,你就喊我‘小弟’就行,幫您跑前跑后,就當我是您在醫院的‘小弟’!”
每當見到自己的新“客戶”時,90后的開封尉氏女孩黃笑迪總會用這樣幽默、爽朗的開場白“破冰”。專職做陪診師前,笑迪在一家電商公司做運營兼客服,所以具備很強的“社牛”屬性。她驕傲地表示:“患者見了我,不用見大夫,病就好了一半!”
“怎么入行呢,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笑迪表示,前幾年,母親患上尿毒癥,陪母親看病、透析、走慢病報銷、取藥,一系列流程下來,自己已經“久病成醫”,對醫院的各種機制、程序摸得滾瓜爛熟。
沒想到,自己的經驗很快就派上了用場。2020年年初,笑迪老家的閨蜜懷孕了,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地工作,她就毛遂自薦,熱心地擔當起陪同閨蜜產檢的工作。
“好心的女孩運氣都不會差”,笑迪表示,自己在陪同產檢的同時,有了意外收獲。在和護士攀談時,護士的一句話點醒了她:“你對醫院各項流程這么熟,可以考慮做陪診員啊!”
“每次去醫院辦事,總會遇到很多老年人、或是外鄉人向我詢問怎么掛號、在哪排隊這些問題。”雖然笑迪每次都熱心詳細地解答,但對方仍然會像“聽天書”一樣,說再多都是一知半解的狀態。“我潛意識里認為,應該有這么一個工作,就是病患就醫的向導,只是沒想到,竟然真有這樣的一個工種——就是陪診師!”
在那名熱心護士的引薦下,笑迪先是進入了一個護工群,并接到了第一單工作——一名在上海工作的白領,委托她帶領自己獨居鄭州的母親,做術后復查。
笑迪憑借熱情開朗的性格“一戰成名”,徹底征服了第一單客戶,“阿姨復查后,還很認真地詢問我結婚了沒有,動了為兒子征婚的念頭!”雖然最終“婚事”沒成,但笑迪卻因此打開了自己的“業務渠道”。
受訪者供圖
收入:“沒外界傳得那么離譜”
本來,笑迪只是本著“認知變現”的“玩票”思維,兼職做這項工作,然而做著做著,她越來越知不足,開始投入到這項工作里。
“陪人體檢,病人忽然低血糖了,當時我都蒙了,不知道什么情況,也不知該怎么辦,只能狂奔著找大夫!”笑迪說,隨著陪診工作越來越多,自己的欠缺和不足之處也越發凸顯:緊急情況如何處理,疑難雜癥該歸到哪科,醫保報銷卡在哪里,這些都需要認真學習提前準備……
為了能勝任這一角色,笑迪干脆把電商運營的工作給辭了,專心地學習了解陪診相關的知識。后來,每次陪診時,她總會隨身背上一個雙肩包,里面裝有速效救心丸、奶糖、酒精濕巾以及醫用護理包。“會提前了解患者的情況,提前有針對性地進行裝包!”
在患者的口口相傳之下,笑迪把電商理念運用到陪診業務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私域流量”——為陪診建立的微信群里面,固定客戶就有幾十個!
“在患者中間口碑這么好,你做這一行月收入能有多少呢?”
“別提錢啊,提錢傷感情!沒外界傳的那么離譜!”面對記者提問,笑迪打趣地說。盡管如此她還是認真地算了一筆賬,陪診工作主要按照付出的時間來計算的,一般是半天200,全天300元,有其他比如取藥送藥、幫手術患者遞送物品等需要按次付費,“在工作量比較飽和的情況下,每月的進項大概有七八千元,”笑迪坦言,自己的薪水,在行業中處于中上等,“主要我不喜歡多線程作戰,就是安排開時間,同時為好幾位患者服務——那樣會讓自己疲于應付,也服務不好每名客戶。”
故事:陪中年大叔獨自赴京手術
作為專職陪診師,笑迪平日的工作就是幫患者代預約、取號,陪同候診、檢查等醫療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她見證了各種人情冷暖、悲歡離合。最讓她最難忘的,是去年秋天陪一名大叔轉診到北京進行手術的經歷。
“這位大叔不到50歲,是一名私營企業主,還算比較有錢。原以為像他這樣的年紀和成就,不會有太多困難和煩惱,然而我錯了!”笑迪回憶道,在第一次見面時,這個客戶就哭了。
原來,這名大叔患有很嚴重的心臟病,需要盡快轉診到北京進行救治。笑迪說,大叔上有年逾七旬的父母,下有還在讀高中的孩子,所以這次手術“上要瞞老,下要瞞小”,要以去北京出差的借口,偷偷的把手術做了。“擔心不了解當地的醫療體系,也確實需要有人照應,在朋友的推薦下,他找到了我。”
被大叔打動的笑迪,毅然陪同大叔到北京一家醫院就診、住院。原以為一周內就能完成的工作,最終她整整留在北京了半個月。“全國各地患有疑難雜癥的患者都往北京扎,所以在北京手術你要排隊,這個過程是很漫長的,”笑迪說:“在這期間,大叔把我當成家人一樣對待,住進病房里還經常問我在外面怎么吃飯啊,能不能休息好什么的。我第一次感覺到——這個工作,能讓原本陌生的兩個人相依為命!”
“最終,大叔被推進了手術室,經過七八個小時后順利推進ICU”。笑迪回憶,手術前,大叔給每個家人都通了電話,以盡量正常的語氣交代了很多很多。
笑迪再次接到大叔電話時,已是半個月后,大叔從ICU轉進了普通病房,需要笑迪立即動身前往北京為他辦理出院。見到大叔那一刻,笑迪差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原本高大挺拔的中年人,術后消瘦佝僂的如同冬日的枯樹干……
“這下瞞不住家里人了……”大叔一句話,讓笑迪眼眶濕潤。
尾聲:換個心情,告別陪診工作
今年6月,笑迪正式告別陪診師的工作,和朋友合伙開了一家瑜伽館。“陪診師的工作有它的弊端,內卷太嚴重、不是太正規,還老被醫生護士當成黃牛,”她笑言:“這些倒還在其次,主要是做陪診工作,見證了太多的悲歡離合——你不投入進去干,干不好;你投入進去,感情上受不了。我這么開朗的人,都快被弄得抑郁了!”
笑迪說,陪診師的工作,在替患者跑腿走手續之余,也是一個見證者,“網絡曾流行一張‘孤獨等級表’,其中患病還要獨自面對,被排成了終極孤獨。”笑迪說:“所以,干這一行我就總是會被提醒,人生的苦大于樂!就像看了一出撕心裂肺的悲劇后,你總得緩緩,刷刷短視頻、看看脫口秀,所以,我告別了陪診師的工作,盡管我知道我干得還不錯!”
雖然她告別了這個行當,但是回憶起這段特殊經歷時,黃笑迪更多的是難忘陪伴別人熬過求醫的日子,帶給別人溫暖,自己也收獲了美好。
-
世界快看點丨鄭州市市場發展中心全力筑牢疫情“防控網”,守好市民菜籃子
頭條 22-11-10
-
關注:新鄉天力鋰能:子公司天力循環已開始試生產,生產的碳酸鋰以自用為主
頭條 22-11-10
-
今日精選:李佳琦失去“全網最低價”并不是一件壞事 | 2022雙11
頭條 22-11-10
-
每日熱議!一次不用跑,個體戶、靈活就業者可在支付寶繳納社保費
頭條 22-11-10
-
今日播報!201地擬入選“四好農村路”全國示范縣,河南7地上榜
頭條 22-11-10
-
證監會12386網絡平臺正式上線 暢通投資者訴求反映渠道
頭條 22-11-10
-
當前動態:多家銀行行長、副行長任職資格獲批
頭條 22-11-10
-
風神股份擬出資6.12億元,實施巨型及特種工程子午胎改擴建項目
頭條 22-11-10
-
河南省市場監管局發聲:網絡交易經營者應設計簡單易懂的促銷規則
頭條 22-11-10
-
每日熱訊!鴻海董事長談歌爾丟單:不評論對手,鴻海競爭優勢不受影響
頭條 22-11-10
-
關乎中小企業和種業!河南成功對接兩只國家級基金
頭條 22-11-10
-
熱議:鄭州航空港區發布疫情防控期間就醫告知書
頭條 22-11-10
-
全球微動態丨河南:支持南陽打造豫西南應急產業示范基地,助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設
頭條 22-11-10
-
仕佳光子、河南資產等聯合設立光電子產業基金
頭條 22-11-10
-
全球看熱訊:速查!濟源示范區公布4名重點風險人員活動軌跡
頭條 22-11-10
-
1.1萬人!Meta史上最大規模裁員開始,員工將獲得4個月基本工資遣散費
頭條 22-11-10
-
微動態丨南陽市50強企業和高成長30強企業名單發布
頭條 22-11-10
-
世界聚焦:開封市文化旅游投資集團擬發行8億元私募債,已獲深交所通過
頭條 22-11-10
-
每日熱訊!國家衛健委:昨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133例,新增本土無癥狀感染者7691例
頭條 22-11-10
-
滎陽市通告:調整部分區域風險等級
頭條 22-11-10
-
前三季度鄭商所累計成交量國內第一
頭條 22-11-10
-
動態焦點: 隔夜歐美·11月10日
頭條 22-11-10
-
【獨家焦點】河南省首座220千伏智慧變電站建設工程在鶴壁開工
頭條 22-11-10
-
立方風控鳥·早報(11月10日)
頭條 22-11-10
-
直擊鄭州富士康一線 | 員工公寓來了中醫醫療隊!
頭條 22-11-10
-
長葛發布通告:主城區實行3天靜態管理
頭條 22-11-10
-
直擊鄭州富士康一線 | 員工喝上了“中藥包”
頭條 22-11-09
-
洛陽國晟集團申報發行45億元企業債
頭條 22-11-09
-
世界時訊:立方風控鳥·晚報(11月9日)
頭條 22-11-09
-
每日快播:京東CEO徐雷:數實結合的京東更善于幫助實體企業轉型升級
頭條 22-11-09
-
環球熱消息:稀土調價議案恐再次翻車?包鋼股份、北方稀土公告提示風險
頭條 22-11-09
-
當前快看:史秉銳到濟源東區調研,事關呼南高鐵濟源站擬選址區域等項目
頭條 22-11-09
-
鄭州投資控股增持1.03億股鄭州銀行股份,持股增至6.69%
頭條 22-11-09
-
河南金融機構參戰“雙11”花式助消費
頭條 22-11-09
-
焦點信息:中央財政提前下達2023年農業相關轉移支付2115億元
頭條 22-11-09
-
當前動態:河南啟動“十四五”能源領域科技創新項目征集
頭條 22-11-09
-
想要更穩定的經營業績 今年雙11主播流行跨平臺直播
頭條 22-11-09
-
鄭州多家銀行出臺延期還貸政策
頭條 22-11-09
-
南陽投資集團年內首期中票明起申購,規模最高6.6億元
頭條 22-11-09
-
莊建球調研豫光金鉛等,強調拉長產業鏈條,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頭條 22-11-09
-
全球聚焦:三門峽:核酸檢測平臺將維護,期間暫停查詢結果等功能
頭條 22-11-09
-
首破百億!濟源示范區年內貸款余額增量已達102.5億元
頭條 22-11-09
-
響應監管要求,多家國企重組財務公司
頭條 22-11-09
-
恒星科技擬定增募資6億元,用于金剛線擴建等項目
頭條 22-11-09
-
環球快消息!創投日報(11月9日)
頭條 22-11-09
-
豫資控股擬轉讓旗下新興產業基金份額,規模1500億元
頭條 22-11-09
-
鄭州市財政局:充分發揮專項債資金、平臺公司、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等價值
頭條 22-11-09
-
焦點熱文:北京優化完善進返京防疫政策和遠端管控措施 拓展微信公眾號線上辦理渠道
頭條 22-11-09
-
每日速看!漯河召開市長議事會:依托中原食品實驗室,建設食品科創園
頭條 22-11-09
-
許昌一機構暫停接收核酸樣本?剛剛,企業回應
頭條 22-11-09
-
天天熱資訊!占地485畝,商丘動車存車場工程開工
頭條 22-11-09
-
疊加A股震蕩下行影響 10月標品信托成立規模再度下降
頭條 22-11-09
-
世界熱訊:低于市場價20%!11月11日,焦作儲備豬肉開始投放
頭條 22-11-09
-
今日熱訊:鄭州北三環東延隧道將進行夜間封閉施工,為期一個月
頭條 22-11-09
-
每日看點!背靠五糧液集團 宜賓商行啟動赴港上市計劃
頭條 22-11-09

- 象·面孔 | 陪陌生人看病的鄭州“90后”2022-11-10
- 雪景預告|注意了!入冬第一場雪即將抵達老2022-11-10
- 河南本周末氣溫大跳水,陣風最高達9級,山2022-11-10
- 天天看熱訊:來欣賞吧!大河村遺址博物館“2022-11-10
- 【全球獨家】疫情防控經濟發展兩手抓!鄭州2022-11-10
- 筑牢疫情“防控網” 守好市民“菜籃子”2022-11-10
- 【世界速看料】注意!明天全能型冷空氣攜大2022-11-10
- 環球動態:男子酒駕新車遇查先掏手機拍照:2022-11-10
- 當前快報:又上電視了!熱播劇中出現長沙理2022-11-10
- 差 0.5 厘米就刺中心臟!緝毒一線真實畫2022-11-10
- 環球新動態:全國本土新增感染總數激增,42022-11-10
- 音樂劇《唐朝詭事錄之曼陀羅》11 月 11 2022-11-10
- 快播:哄抬價格、未明碼標價 呼和浩特多家2022-11-10
- 環球看熱訊:“世界第一高人”曲折求愛:曾2022-11-10
- 世界快看點丨鄭州市市場發展中心全力筑牢疫2022-11-10
- 關注:新鄉天力鋰能:子公司天力循環已開始2022-11-10
- 今日視點:2022武漢企業百強公布!入圍門檻2022-11-10
- 環球熱頭條丨許昌市公路事業發展中心積極做2022-11-10
- 今日精選:李佳琦失去“全網最低價”并不是2022-11-10
- 每日熱議!一次不用跑,個體戶、靈活就業者2022-11-10
- 天天頭條:許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深入轄區開2022-11-10
- 全球資訊:北漂騎手月入2萬買138平新房,跑2022-11-10
- 今日播報!201地擬入選“四好農村路”全國示2022-11-10
- 新消息丨武漢社區“幸福食堂”日均供菜20種2022-11-10
- 天天速讀:駐馬店市城市書房開展“走進消防2022-11-10
- 新鄉市獲嘉縣:積極開展政務服務事項辦件數2022-11-10
- 【熱聞】商丘城鄉一體化示范區:“三心服務2022-11-10
- 世界時訊:掌摑男童推倒老人被刑拘 為人處2022-11-10
- 南京鼓樓肛泰中醫醫院:半夜胃疼醒,是怎么2022-11-10
- 南京鼓樓肛泰中醫醫院:經常胃脹氣很難受,202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