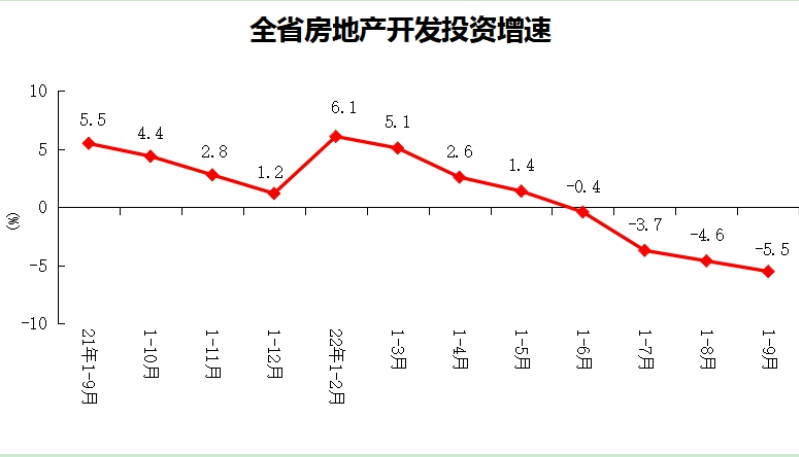毛紅芝人生中第一次蹦迪,是在76歲時。
終于能有一個片刻,打破她寂靜的生活。大概是耳朵不行了,她也沒覺得吵。身上的膏藥守護著她的安寧,勁爆的音樂能帶給她快樂。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那個下午,她換上衣柜里最鮮亮的衣服,離開空蕩的家,騎車到村南頭的空地上,和上百個老人一起“蹦野迪”。舞動的人群中曾有上百種孤獨,當音箱的旋鈕一轉,就只剩一種快樂。
在安徽宿州蕭縣毛郢孜村, 28歲的王明樂幾乎花光積蓄,組織起這樣一場狂歡聚會。年紀最大的參與者,已有94歲。每天下午1點至2點,他們像上班一樣準時來到王明樂家。聚集的人從院子里溢出來,延伸到門口、院前,又到兩旁的村道上。
他們跳舞、聊天、打牌、吃飯。如有缺席,還會托人帶請假條來:“杜金花收玉米一天。”“王盛英今天下午不去,不得閑,栽菜籽。”
一
說是蹦迪,其實沒有人能真正蹦得起來。
七八十歲的身子骨,總有一只腳得穩在地上。硬朗些的,能扭兩步秧歌,其他多數是原地踏步。手是相對自由的,盡情舉高了往前甩,向兩邊揚。或者叉在腰上,像做保健操一樣扭屁股。
實在站不穩的,雙手向前拄著拐杖,兩腳岔開,在地面上構成一個穩定的三角形后,搖頭晃腦地扭胯。動作和他們的關節一樣僵硬。
蹦迪的音樂要足夠大聲,才能穿過他們聽力減退的耳朵,讓他們忘記羞澀,忘記年齡。王明樂則站在音箱上,跳躍著帶動氛圍。
老人的動作不似年輕人奔放熱烈,但狂歡的勁頭仍有的一拼。
75歲的盧彩霞患有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跳一次不僅腰疼,連帶著腿、腳脖子、腳心都疼。即使這樣,走不了路,她騎自行車也要去跳。
毛紅芝一條右腿5樣毛病:腫瘤、關節炎、滑膜炎、骨裂、積液。白天口服藥,夜里貼膏藥,也要去跳。不僅要跳,還要換一身紅紅綠綠的漂亮衣服,站第一排跳。“我就愛動彈,我不喜歡往那里一坐。我就愛跳!愛蹦!”
王明樂給她一只掃把,讓她當吉他彈。有人問起,她會驕傲地說:“我是琵琶手。”
這個年輕人帶著他們見足了世面,還去過KTV。他們跟著王明樂坐電梯,進入黑乎乎的包廂,在“閃閃光光的燈”下跳舞。毛紅芝覺得,跳起來比村里“有勁兒”,“跳得淌汗還想跳”。
來自孤山村的女人劉富榮,經常騎著電動車往返40分鐘,來毛郢孜村跳舞。她46歲,一頭短發染成黃色,身型微胖,是隊伍里最年輕的、能雙腳離地的舞者。
她的舞姿是不顧一切地——瘋狂地搖頭,甩起的頭發似火苗躍動,身體像觸電一樣晃動,四肢肆意地甩。她完全放松,跟著音樂釋放自己,家里那些要壓垮她的事,“一點兒都不想”。
音樂結束,毛郢孜村又回到寂靜里。人們拎著板凳,騎著車,各自散去。
劉富榮渾身濕透,“像做了一場夢一樣”,醒來重新面對她的生活。幾年前,她帶著患有自閉癥的兒子改嫁到這里,和一個比自己大9歲的男人生活,生了一個小女兒,已經上幼兒園了,但兒子還是連一句“媽媽”都不會喊。她和丈夫共用一部老年機,不通互聯網。在朋友的手機上,她才看到王明樂組織的活動。
二
王宗云回到家里,重新面對一屋子的紙箱。
一張空床,幾乎讓大大小小的紙箱堆滿了。它們曾裝過三個兒子和幾個孫子從全國各地寄來的吃食、衣物與日用品,光燒水的電水壺,家里就堆了三四個。王宗云覺得自己“前面的路沒有多長了”,“不想要,什么都不想要”。
她80歲了,收到最多的還是藥。護腰的、保心的、治胃的……有些常用藥,一寄就是40盒,“沒有藥我就不能活”。兒子怕她拉肚子,寄來10盒諾氟沙星膠囊。
王宗云隨兒子在山西生活了一二十年,幾年前才回到毛郢孜村。她在院子一角種了許多菜,但這里仍讓人感到荒蕪。
丈夫是去年10月走的。那個冬天,王宗云哭得“兩個眼都看不到啥了”。她嫁來這個村子60年,第一次“沒有了一點靠頭”。她生了4個兒子,如今只有老三因為精神問題需要照顧,留在她身邊。其余的孩子都忙,大兒子路過徐州去開會,也沒下車,只打了個電話來。王宗云理解,也不理解:“就忙得這么狠,就忙得這么狠……”
盧彩霞的三個兒子分別生活在山西、河南、山東。她和老伴兒干了一輩子,給兒子們娶了媳婦,落了幾萬元的賬。兩人去徐州打工11年,“賬還清了,也累病了。”去年,老伴兒因胃癌過世,盧彩霞“一張嘴說話就想哭”。
后來,她也不愛回那個家。“我不想擱家蹲,我自己在家是個啥味兒?”她簡單吃口飯,就出門找人“拉呱”(方言,指聊天)去了。
毛紅芝直到71歲,才結束自己的打工人生,從徐州回到村里。
她住的房子是三個兒子結婚分家后,自己另蓋的。那時,她和丈夫種菜賣菜為生。再往前,在沒有電視機的年代,她的丈夫跑村串鄉,放了15年電影。毛紅芝是村里少有的上過初中的女人,她當過村里的會計、老師、民兵,喜歡唱歌跳舞,能打籃球。
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兒子們結婚后不久,丈夫就患了肺結核,沒法再做重活兒。毛紅芝不愿給兒女增加負擔,只身去了徐州打工。一早一晚拾破爛賣錢,其余時間當保姆。20年間,她先后伺候送走了3個老人,直到她自己也老了。
退守回村,生活難免不適應。多年的務工經歷,讓毛紅芝有了城市生活的習慣。她愛在人民公園里跳、唱、打羽毛球。回村時,她還把羽毛球和球拍帶了回來,但很少再用。
去年,毛紅芝的老伴也走了。她倒是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只是覺得無趣。因此每天在外面的時間比在家里多,哪怕幾個人坐著,也比一個人坐著好。
毛郢孜村常住人口3605人,60歲以上老人占比約四分之一。他們的休閑方式,就是把板凳搬出來,坐在外面。一戶大門,一個老人。有的門前能聚兩三個人,一塊坐著聊天,聊著聊著就沒話了,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對著發呆,看看天,“沒有一點兒熱鬧勁”。
三
不如跳舞。
冬天跳舞能讓老人們暖和起來,發發汗。但夏天太熱,容易“跳出毛病”。王明樂就組織他們打牌、唱歌,在自己家院子里聚會。
每天下午1點到5點,這里會涌入五六十個老人。腿疼的騎車,頭暈的走路。下雨天本是不去的,到了中午,雨剛停一會兒,人插著空又來了。
這幾個小時,院里到處都是說話的聲音,空氣里縈繞著低沉的嗡嗡聲。他們聊的內容,王明樂并不感興趣。家長里短的,他甚至聽得頭疼。
帶一群老人,有時和帶一群孩子沒什么差別。他們容易為極其瑣碎的小事吵架、鬧脾氣。“跟幼兒園一樣。”
每天聚會結束,老人們會把自己的椅子藏起來,第二天來了,再找出來坐。王明樂家里經常這兒一把椅子,那兒一把椅子。他看到了也不去挪動,“就讓他們藏著”。
老人們散去之后,院子里又只剩王明樂一個人。
他的父親是下井工人,常年在礦上住。妹妹也已經出嫁。他本來和母親同住,但2018年2月的一場車禍帶走了她。
悲劇發生得太突然。母親出事前一天,王明樂下班晚,他買了一大把母親愛吃的香蕉,忘在車后備廂里,還沒有拿出來。
從那天起,家里變得極其安靜。只少了一個人,就好像“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王明樂回家習慣了喊“媽媽”,后來,這兩個字噎在嗓子眼里不上不下,“喊不出來”。
為了打破安靜,他總是開著電視。母親生前養了只花公雞,他把它抱在懷里,和它一起看電視,給它起名“花花”,為它洗澡,允許它進入客廳,被它打鳴吵醒也不翻臉。
這恐怕是毛郢孜村唯一一只成為寵物的雞,它出去溜達,方圓幾里的人都認得它,走丟了也能找回來,“大家知道是我家的雞”。村里的老人私下議論,“他可能腦子受了點刺激”。
為了讓家里熱鬧點,王明樂又養了兩條狗、9只鵝、5只鴨子、數十只小貓和二十幾只小雞崽。滿院子都是嘰嘰喳喳的聲音。
即使最孤獨的時候,王明樂也沒想過離開村子。這里讓他感到踏實,“有根”。但和他一起守著“根”的,大多是老人。
2020年12月,王明樂開始組織村里的老人跳舞集會,拍各種稀奇古怪的抖音視頻。他在村里認識的老人不多,說過話的也就十來人。于是就用幾根煙“拉攏”老頭,又搬幾筐雞蛋“引誘”老太太。就這樣幾個人慢慢變成十個人,又變成幾十上百的人,直到全村都知道了,周邊的村莊也知道了。
人越來越多。王明樂的院子幾乎成了全村的情報中心,連父親要再婚的消息,他也是聽老太太們說的。從小到大,他和父親的交流都不多,“說一兩句話,就吵起來了”。
后來父親真的從礦上回來,跟他說“收拾收拾辦事情”。王明樂就理解了。他覺察到父親的難堪,但兩個人都沒多說什么,匆匆辦了酒席。“畢竟才50歲,以后老了有個人陪他也是挺好的。”他也難掩失落,“感覺以后再也沒有從前那樣的感情了。好像分了兩個家一樣,沒有一個家了。”
四
母親離世后,王明樂一直穿著她給他買的鞋。
五六個春夏秋冬穿過去,那雙帆布鞋已經看不出原本的顏色,成了泥黑色。帆布爛卷了邊,兩只腳的大拇趾都露在外面。
這雙鞋一年修了4次,還被狗叼走丟過一只,他花200元在朋友圈“懸賞”求助又找回來。老人們把這鞋藏起來,又給他做新的棉鞋,他都不肯舍棄。
王明樂對母親的懷念,帶著沉重的歉意。她是一名代課教師,從小對王明樂管束嚴格。“別的小朋友都在外面,她出門前會把門鎖上,把我關在屋子里。有時候我翻墻頭出去,回來就是一頓打。”
他反而更好奇管束之外的世界。小學就學會了抽煙,初中又逃課上網。他轉過5次學,最后來到一所只有6個學生的鄉村中學,“沒事兒都跟老師一塊斗地主”。
沒讀完初一,他就輟學了。后來,他去了北京,端過盤子,在工地上扛過水泥,也試圖學過導游,沒有學成。回鄉后,他又打了幾年工,用積蓄買了輛車,開始做代駕生意。
母親去世后,他經常寫字懺悔:“從小到大你對我很嚴厲,動不動就會用棍棒伺候我,小時候真的很恨你,長大了自己也有自尊,犯錯了,就會用你以前怎么對我不好來襯托我的錯誤。真的,真的,我從來沒有恨過你。我很愛很愛你,年少無知真是錯。”
為了控制自己“胡思亂想”,王明樂拼命工作,“像野人一樣活著”。之后兩年,是他的事業巔峰期。代駕公司最多時有五十幾個員工,每天凈收入兩三千元,他干到凌晨四五點才回家。后來,他又開始賣酒、賣葡萄,賺得更多。
他拿著這些錢拼命地做好事,希望讓母親能看到自己的改變,能為自己驕傲。
為了替母親盡孝,王明樂把外公接過來和自己住了一兩年,變著花樣給他做菜。村里一個老太太和兒子吵架,兒子想把家門口的一摞磚送人,老太太想留著賣錢。王明樂無意中聽到,花200元買下了這堆無用的磚頭,又轉手送給了別人。“就想讓他母子倆關系好一點。”
他和老人蹦迪的故事被媒體報道。王明樂希望母親能看到這一切——兒子“上電視了”,“應該會開心吧?在我們農村能上一次電視,也不是多么容易。”但轉念又想,她可能還是不滿意,“沒掙到錢,只花錢了,她肯定不開心。”
五
連王宗云的兒子也知道,王明樂這幾年花了不少錢。
KTV包廂一小時的費用是50元。給老人做一頓小雞燉蘑菇,光買蘑菇就得300多元。組織吃一頓早餐,包子、雞蛋、粥,三樣買下來280元。用毛紅芝的話說,“再不值錢,也擱不住多!”
毛郢東村家境困難的老人,幾乎都收到過他送的米、面、油、奶。組織蹦迪后,他隔三岔五給老人發日用品。冬天發面霜、羽絨服、水餃、掃把、尿桶、刷碗手套,“洗碗不凍手”。夏天發毛巾、內衣、牙刷、肥皂,“洗澡能用”。最近天冷了,他又花600多元買了個燒開水的設備,放在院子里讓他們喝水。
王明樂注冊了一個抖音賬號,在上面更新分享和老人的快樂日常,粉絲20多萬,沒接過廣告,也不帶貨。連毛紅芝也想不通:“樂樂,你的目的到底是啥子?”有記者來訪,她拽著他們小聲問,“能不能給他找個工作?”
王明樂說,自己這幾年來大約“花了五六十萬元”在老人身上,幾乎掏空了存款。疫情以來,他的代駕生意冷清了許多,公司只剩十來個員工。“大家都不怎么出去吃飯喝酒了。”他囤的酒也賣不出去,每天在朋友圈發廣告。
壓力大的時候,他凌晨三四點才入睡。早上8點半就被鬧鐘叫醒,穿上衣服,臉也不洗,就出去擺攤賣酒。
他想過放棄這場聚會。但第二天,老人們一如往常地到來,看到他們,“就舍不得了”。有次他去北京代駕辦事,跟老人們說好“不要來了”。第二天下午,王明樂從家里的監控上看到,他們還是陸續來了,“就在我家門口的石柱上坐著。”他本來計劃在北京多轉兩天,后來“直接就回去了。”
王明樂出門送酒,幾個老年牌友就在家門口給他打電話,問他什么時候回來,晚上一起打牌。他們總要打到晚上10點多。有的老人愛耍小賴皮,把壞牌偷偷往牌堆里塞,贏了牌就手舞足蹈。王明樂喜歡他們這樣簡單的快樂。
一面是經濟負擔,一面是情感負擔。他在等一個機遇,能讓自己承擔目前的開銷,又把好事繼續做下去。
六
很多人都期待著這場聚會。起初只是人來,王明樂組織集體做飯后,他們把廚房也從家里搬了出來。
一個人生活,做飯是最難的。盧美霞換了小電飯鍋煮飯,還是一煮就多。做一頓,吃一天。菜也“劃不來做”,偶爾勤快了,炒點蘿卜白菜,多半時間配咸菜吃。
毛紅芝房前屋后都種了菜,豆角、黃瓜、辣椒、南瓜……啥都不缺,唯一的問題是吃不動。人老了,消化也慢。中午1點之后,她就很少吃東西了。那一塊菜地,既養活自己,也養活王明樂家的雞鴨鵝。吃過午飯,她把地里的爛菜葉子都收拾起來,就“上樂樂那兒熱鬧去了”。
盧彩霞老伴離世前,為她劈好了幾年用的柴火,整整齊齊摞起來,用塑料布捂著。她覺得自己燒不完了。開澡堂的人來買,她沒賣,而是陸陸續續往王明樂家拉了七八車。
一群在家連菜都不想炒一盤的人,心甘情愿在這里和面、搟面、燒火、烙餅,沒有一道工序是簡單的。皖北的鏊烙饃薄且筋道,他們也不關心自己的牙口還咬不咬得動,只管興高采烈地做。
人最多的時候,能分出19個烙餅攤。柴火燒起來,整條村道都是煙,人的聲音都給搟面杖和鍋熗子淹沒了。王明樂為他們提供面粉,烙好的餅,每人能分一二十張,帶回家足夠吃一段時間了。
有時,王明樂就在院子里架幾口大鐵鍋,燉雞燒菜,備140多雙碗筷,叫他們來吃。
今年夏天,他在午后三四十攝氏度的天氣里做了一頓飯,第二天就發了高燒。幾個老太太拉他去了村里的診所,等輸上液,圍著他就開始念叨:“你自己又沒個娘……幸虧這里有個人,沒有人,你這不燒毀了?你趕緊找個媳婦照顧你,你叫人心里都好受……”
這兩年來,王明樂很少鎖門。一個老太太從山上挖了地棗苗子,蒸熟端了一盤,推開門就進來了。每逢年節,家里出入的人更多。
今年中秋,王宗云家人又給她寄了一大盒月餅,她也搞不清是誰寄的。她把那盒月餅拆開,拿了6個給王明樂吃。王明樂一看,都是有牌子的“好月餅”,“紅豆沙的,咸蛋黃的,老好吃了。”
七
許多在外務工的人,通過王明樂的抖音看自己的親人。
一位ID名為“靖靜”的用戶經常給他評論:“謝謝六子,又看到俺媽了,跟你們在一起,她說她高興。”她遠嫁河北十幾年,上一次回家的時間是前年9月。
有人在王明樂的視頻里看到了自己的母親,留言說:“我媽真會玩!她身體一直不好,看她這么開心,我也開心!”一個男孩也從烏泱烏泱的人群中找到了熟悉的面孔,“我奶咋在里面?”還有人想不通,“俺奶奶老說腿疼,這不跑得才溜嗎?”
外鄉人在這里表達羨慕:“我老家要是有你這樣熱心的人,我在外面也會放心爸媽。”“我奶奶老了,沒智能手機,沒人陪她,晚上一直盯著表看時間。”
“搖頭王”劉富榮也成了粉絲的一員。
幾個月前,她的丈夫突發腦梗。家里的收入來源斷了,這一小時的快樂也難以為繼。劉富榮只身前往徐州打工,在建筑工地上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錢幾乎全部寄往家里。
下了工,她會去看徐州人跳廣場舞。但那不是她喜歡的音樂,她喜歡“搖滾的”、快節奏的。但看久了,心里也激動,也想跳。她控制自己,“徐州不是家,不能跳,人家見世面多。”自己跳的那些動作,免不了“被人笑話”。
她住在20元一天的小屋里,花350元給自己買了一部舊智能手機,在上面關注王明樂和毛郢孜村仍在延續的熱鬧。
王明樂努力維持著視頻的更新頻率,也接受著“人”的變數。2021年10月5日,他發布了一條視頻,紀念老年舞團中第一位病故的高齡老人——“最左邊坐凳子上,頭上頂個毛巾的奶奶”。那段視頻里,她坐在人群中,看著在音箱上又蹦又跳的王明樂,跟著他弱弱地揮手。
王明樂記得,她笑起來總是很害羞。
-
當前速訊:國家衛健委:昨日新增本土“3041+29654”
頭條 22-11-25
-
世界簡訊:南陽漢文化影視康養項目最新進展:欲打造豫鄂陜三省交界文旅名片
頭條 22-11-25
-
天天快看點丨兩部門發布《違法違規使用醫療保障基金舉報獎勵辦法》
頭條 22-11-25
-
【天天時快訊】成交額4.87億元,鄭州4宗164畝土地完成出讓
頭條 22-11-25
-
恒大突發!11宗地遭政府無償收回,凈用地面積2071.3畝!什么情況?
頭條 22-11-25
-
河南昨日新增本土感染140+719
頭條 22-11-25
-
【環球新要聞】起始價9.97億元!鄭州5宗零售商業用地掛牌出讓
頭條 22-11-25
-
隔夜歐美·11月25日
頭條 22-11-25
-
天天速讀:鄭州經開區發布疫情防控期間市場保供穩價的告知書
頭條 22-11-25
-
焦點要聞:鄭州高新區新增9個高風險區
頭條 22-11-25
-
全球視點!立方風控鳥·早報(11月25日)
頭條 22-11-25
-
鄭州市二七區新增21個高風險區,13個降為低風險區
頭條 22-11-25
-
焦點消息!中州時代觸手可及:寧德時代的洛陽行動 | 河洛觀潮
頭條 22-11-25
-
【新要聞】鄭州市金水區解除一處高風險臨時管控區
頭條 22-11-25
-
環球快報:鄭州市惠濟區新增7個高風險區、6處降為低風險區
頭條 22-11-25
-
“第二支箭”增信首批民營房企債券發行
頭條 22-11-24
-
世界信息:辟謠!網傳南陽市將封城系謠言
頭條 22-11-24
-
看點:歐洲央行會議紀要:75個基點加息步伐得到絕大多數支持
頭條 22-11-24
-
鄭州開放142處核酸采樣屋,方便保供等重點人員核酸檢測
頭條 22-11-24
-
今日訊!登封市通告:14個區域劃定為高風險區
頭條 22-11-24
-
鄭州明日零點再啟“防疫攻堅” 市民買菜儲糧高潮已退
頭條 22-11-24
-
每日熱點:立方風控鳥·晚報(11月24日)
頭條 22-11-24
-
碧桂園獲三家國有大行授信支持 總額度超1500億元
頭條 22-11-24
-
環球關注:河南省研究出臺有關保障措施 全力保障疫情期間群眾基本生活和緊急就醫
頭條 22-11-24
-
環球速遞!再采購1.5萬斤!浙商銀行鄭州分行第三批愛心蔬菜送實體企業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4
-
【天天新要聞】牧原股份:預計明年生豬養殖產能會進一步提升
頭條 22-11-24
-
助農蔬菜進鄭州,通行證怎么辦?保供證明怎么開?答案都在這里
頭條 22-11-24
-
焦點速讀:河南省直住房公積金11月25日暫停實體服務大廳窗口服務
頭條 22-11-24
-
每日精選:南方航空深圳分公司黨委原副書記、總經理劉國軍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頭條 22-11-24
-
觀天下!中央網信辦公布第三批首發謠言典型案例
頭條 22-11-24
-
全球視點!濮陽通告:11月25至27日實行交通管制、每天開展一次核酸篩查
頭條 22-11-24
-
美的置業獲四家國有大行授信支持
頭條 22-11-24
-
環球速讀:鄭州銀行:行長趙飛任職資格獲核準
頭條 22-11-24
-
全球熱頭條丨新鄉出臺建設“創新創業魅力城”三年行動方案,著力打造“兩區兩谷一城”
頭條 22-11-24
-
焦點訊息:近600噸!濮陽一連鎖商超買走濮陽及周邊農戶急售菜 | 財立方助農
頭條 22-11-24
-
鄭州銀行擬發行50億元金融債,債券評級AAA
頭條 22-11-24
-
【全球聚看點】銀保監會介紹六大行落實“地產16條”舉措 建立區域優質房企“白名單”
頭條 22-11-24
-
世界視訊!彭波一審獲刑14年 非法收受5464萬余元
頭條 22-11-24
-
環球微資訊!東航、南航擬發行共35億元超短融,用于償還債務等
頭條 22-11-24
-
焦點!湖北荊門:擬允許分期繳納土地出讓價款 一般企業在1年內繳清
頭條 22-11-24
-
劉忻、張雁云任浙江省副省長
頭條 22-11-24
-
環球訊息:河南省地方金融監管局:批復中原小貸等4家公司變更事項
頭條 22-11-24
-
全球觀焦點:商務部:全國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總體充足
頭條 22-11-24
-
天天快播:《設計南陽建設行動方案》發布,力爭2035年設計產業規模達600億元
頭條 22-11-24
-
天天頭條:鄭州市科技局公示6家高新技術企業受理補充名單
頭條 22-11-24
-
國鐵集團完成發行100億元鐵路建設債券,票面利率3.42%
頭條 22-11-24
-
寧德時代入選全球電池聯盟董事會,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企業
頭條 22-11-24
-
環球精選!總投資20億元,漯河簽約智能傳感器中部生產基地項目
頭條 22-11-24
-
天天快資訊丨河南省開展信用提升行動 助力市場主體紓困解難
頭條 22-11-24
-
世界熱推薦:河南全力保障疫情期間群眾緊急就醫需求六項規定
頭條 22-11-24
-
世界資訊:官宣!濟源市科學院、河南省科學院濟源先進材料產業技術研究院揭牌成立
頭條 22-11-24
-
世界速看:如何做好疫情期間困難和特殊群體關心關愛工作?河南提出8條具體措施
頭條 22-11-24
-
河南昨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59例,無癥狀感染者536例
頭條 22-11-24
-
看熱訊:鄭州:醫療機構正常開診,疫情期間看病就醫有保障
頭條 22-11-24
-
環球視訊!河南省國家物流樞紐增至6個 居全國第一
頭條 22-11-24

- 世界看點:蹦野迪 村口見2022-11-30
- 天天新資訊:摩托上路酷又爽違反交規當思量2022-11-30
- 神舟十五號成功對接空間站組合體2022-11-30
- 今亮點!新一代 LCD 旗艦!iPhoneSE4 將2022-11-30
- 天天熱文:“中國傳統制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2022-11-30
- 【環球快播報】球擴束徑技術輔助弓部三開窗2022-11-30
- 世界觀天下!11月30日起鄭州地鐵調增運力2022-11-30
- 全球要聞: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發射取得圓滿2022-11-30
- 【速看料】申遺成功!祝賀“中國茶”2022-11-30
- 【時快訊】2022 年 11 月廣州出租車、網2022-11-29
- 播報:河北:預計今明兩天最低氣溫跌至零下2022-11-29
- 環球熱門:廣州社會組織組建抗疫“暖心團”2022-11-29
- 環球快資訊丨就在您身邊!廣東公布 20 個2022-11-29
- 關愛·溫暖|網課時的“紙短情長” 鄭州高2022-11-29
- 全球快看:11月30日起 鄭州公交全面恢復運營2022-11-29
- 世界信息:擁擠的地鐵磨人的公交,交通成了2022-11-29
- 環球觀點:溢出屏幕的熱情!從衣服就能看出2022-11-29
- 今頭條!2022 年 11 月廣州市校車交通違2022-11-29
- 玩鷹隼,卡塔爾人的“全民運動”2022-11-29
- 環球簡訊:廣州荔灣“紅色經典誦讀”活動結2022-11-29
- 升降梯折斷高空作業者當場摔死,法院:存在2022-11-29
- C919 大型客機獲頒生產許可證2022-11-29
- 焦點熱文:岳麓書會 | 中小學生“愛讀書2022-11-29
- 關注:夫妻檔舍小家齊上陣,投入隔離酒店抗2022-11-29
- 環球熱點評!“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2022-11-29
- 關愛·溫暖|河南:“織愛行動”助力困境兒2022-11-29
- 全球要聞:降雪量5.1毫米!鄭州飄雪花,這2022-11-29
- 神十五航天員領命出征,祝一切順利!2022-11-29
- 1.66 億元接盤西沃客車 比亞迪新能源版圖2022-11-29
- 全球百事通!又一對恩愛夫妻崩了…2022-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