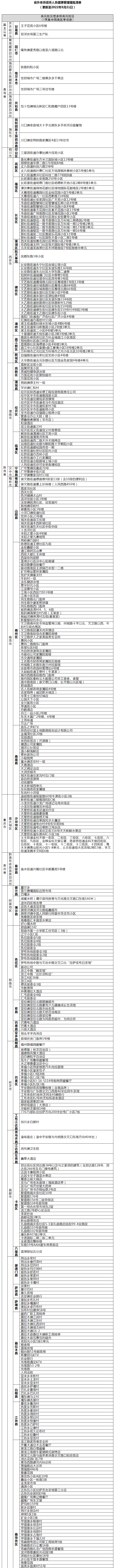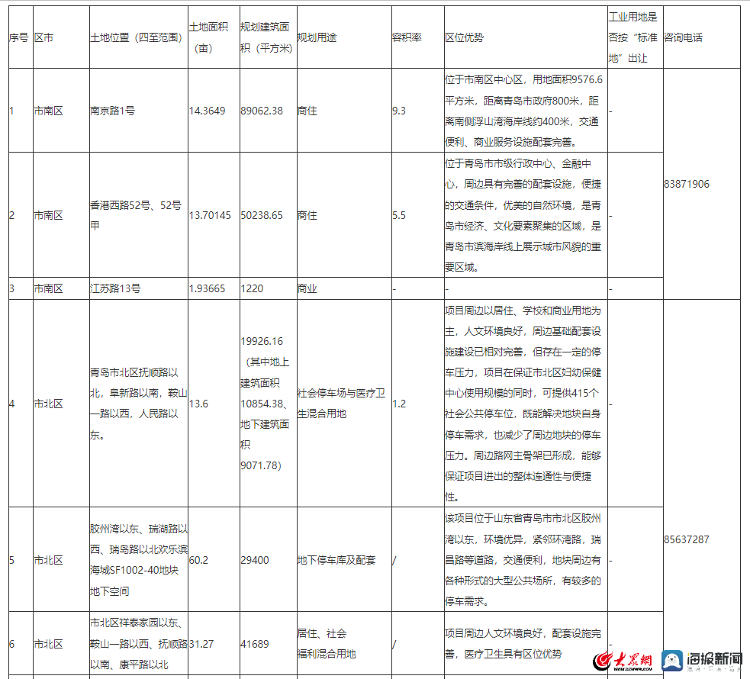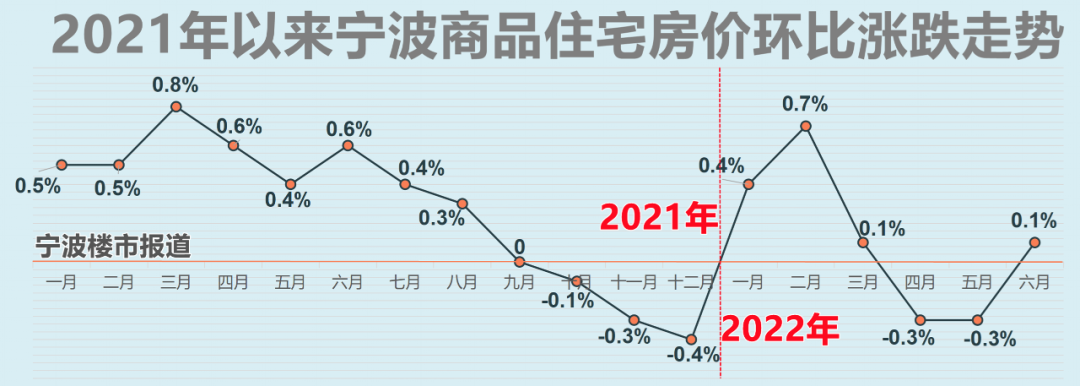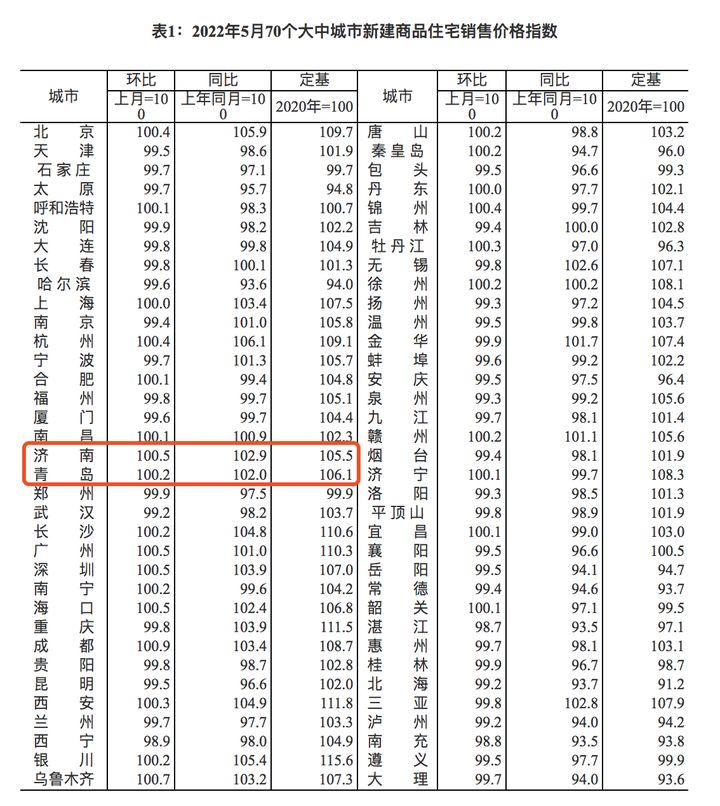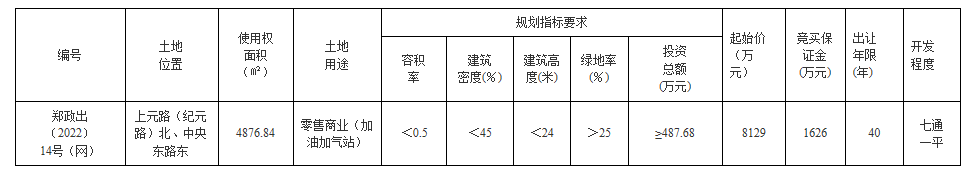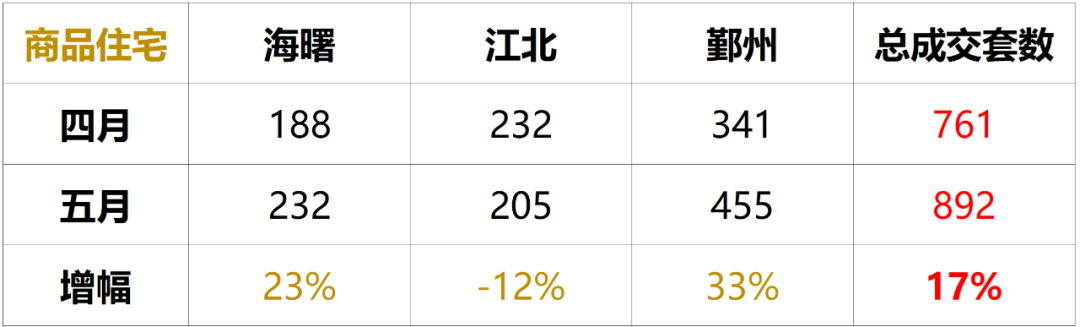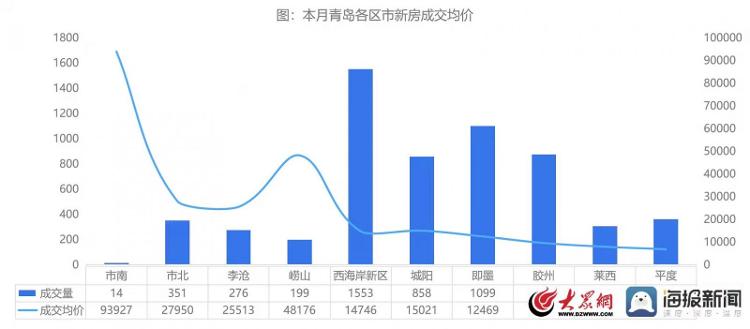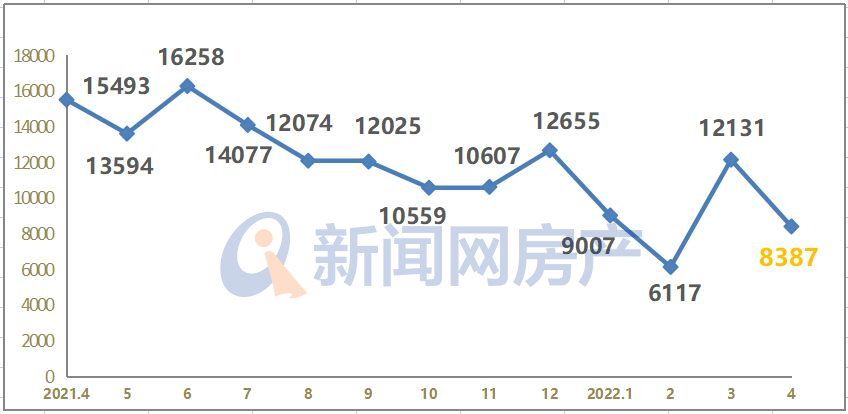“訂單5分鐘后即將超時。”伴隨著系統的提示音,53歲的王計兵停車、奔跑、上樓。他氣喘吁吁地按響門鈴,將外賣遞給了門縫里伸出來的手。
關門的瞬間,靈感在他腦海中閃過。他興奮地掏出紙筆記下,又一首詩的雛形誕生了。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過去的4年里,他在送外賣時創作,思緒隨著高速行駛的電瓶車上翻飛,靈感滋生于等商家出餐的間隙、顧客關上門的瞬間、午夜送遠路單的路上。
7月下旬,隨著作品《趕時間的人》出圈,王計兵走紅。網友評價他的作品寫得深刻,是“勞動者之歌”。
贊美的另一面,是他被生活反復捶打的前半生。
經歷了輟學、貧困和誤解后,他形容自己是一枚被重新取直的釘子,“生活有的時候會把你撞得變形,我是被敲擊完了,自己把自己取直的。”
工作中的王計兵。 圖/受訪者提供
【1】趕時間的人
凌晨5點30分,手機鬧鐘準時響起。王計兵醒來,洗漱,騎車出門。城市尚未蘇醒,路上還沒有行人,但他要趕去自家商店開門營業,迎接第一批上學的學生。
臨近中午,妻子來到店里換班。他往外賣箱里丟了兩瓶礦泉水,然后打開系統,騎上電瓶車,開始接單。
昆山夏天的氣溫直逼40度,但王計兵習慣了,他不能錯過午高峰,“這是跑外賣最重要的時候。”
城市的間隙,有許多和他相像的外賣騎手。因為常年在戶外暴曬,他們通常皮膚黝黑。如果觀察仔細,可以在部分人身上發現或大或小的傷疤。這可能是某次雨天,電瓶車打滑摔的。
7月20日,王計兵的詩歌《趕時間的人》被媒體人陳朝華分享到微博,引發關注。網友評價他的作品寫得深刻,“是勞動者之歌”。
突然的走紅,讓他有些惶恐。他覺得自己的詩談不上深刻,只是對生活現象的記錄,“我就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個人,有了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愛好。”
“普通”的王計兵,從2008年開始寫詩。據不完全統計,他創作的詩歌有3000余首。寫詩的時間和地點不固定,在顧客關上門的瞬間,也在疾馳去送餐的路上。靈感閃現時,他就在微信文件傳輸助手給自己留言,空閑時再整理成詩。
最讓王計兵興奮的是夜間送去郊區的送遠路單。他享受長途行駛時車輛不斷加速的過程,“它給你的這種自由感,就像鳥兒展翅那樣。”返程不趕時間,他會選一條漆黑的小路上,“這時候,你每一個響動都是驚天動地的,感覺整個天地都是你的,有一種巨大和渺小的對沖。”
但悠閑只是少數,大部分時間里,外騎手和時間的賽跑,從接單的那一刻開始,《趕時間的人》記錄著他的焦灼。
“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個地名/王莊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個個飛奔的外賣員/用雙腳捶擊大地/在這人間不斷地淬火”
這首詩的雛形,誕生于一份留錯地址的訂單。當時,他要去一個老舊小區的6樓,沒有電梯。第一次,顧客留錯樓號。第二次,單元號填錯了。等到他終于敲對了門,卻聽到顧客劈頭蓋臉的數落:“你是怎么送外賣的?”
這一單,他上上下下共爬了18層樓。本可以輕松完成手上的三份訂單,“結果被他那一趕,連著后面的兩單都給趕成超時的。”
最極端的一次,王計兵說他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脅。一名女顧客將地址錯填到了前男友家,王計兵被醉酒的男顧客當作了發泄對象,“他抓到我的領口,幾乎是拎著我在他們房間里面轉圈,我就感覺到快要窒息了。”
王計兵決定隱忍。他害怕顧客的投訴,因為平臺會罰款,一次50塊,“相當于半天的工資都要白干。”他也很少會為自己申訴,因為平臺要求回到相關地點拍攝帶水印的照片,“有這時間,我可以完成另外的單量,把這損失又彌補回來了。”更何況,申訴的成功率往往不到50%。
在他看來,事故、罰款和投訴是作為騎手這個職業需要承擔的風險,“你既然端了這碗飯,它里面有沙子,你也要吃它,有米你也吃它,能吃掉就行了。”
2021年,王計兵家的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2】一枚重新取直的釘子
對于騎手這個職業,王計兵始終抱著一份感激,“它讓你很辛苦,但是可以養活家人、養活自己。”
這與他坎坷的經歷有關。“我的生活,一直在碰不同的壁,有的時候會被撞得變形。”他說,自己是一顆被生活反復捶打的釘子,每次被敲彎后又把自己重新取直。
他來自蘇北一個極度貧困的村莊。在這里,讀書是擺脫貧困的唯一捷徑。他學習也爭氣,上學時拿的獎狀一度糊滿了老家的土墻。在他曾經的設想里,自己會考上高中、大學,成為村里飛出的“金鳳凰”。
轉折發生在初二那年。為了改善王計兵的體質,父親將他送到了武校,希望他能文武兼備。正式上課后,王計兵才發現,武校沒有文化課。那時通訊落后,等到他的信寄到家里,父親再趕過來,已經過了20天。
武校不愿意放棄生源,他也錯過了中學的開學時間。他妥協了,“那時候就想,不行就好好學武,到時候能做個教練什么的不也挺好的。”
但生活的第二次捶打很快來臨。在武校的第二年,家里已經很難湊齊他的學費。等到放年假回家,父親跟他攤牌:家里沒錢了,學校不能上了。
“我就突然之間輟了學。”現在回想起來,王計兵忍不住感慨“造化弄人”。
輟學后,他去到沈陽,在建筑隊里當小工。他是隊里最小的一個,虛歲19歲。每天的工作很簡單,“就是扛不完的木頭,扛完這堆還有那堆,扛完這車還有那車。”
他曾設想過兩種未來——考上大學,或者當武校教練。都是體面、穩定的。當這一切都成空時,他嘗試說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樣去生活也可以。
他的參照系是工地上的普通工人。工地上講究師承,普通工人通常會跟著一個師傅學習。“但那你會發現正常生活也很難,你會發現你做不了一個普通人。”
像王計兵這種小工,是沒有師傅的,他們做著最基礎最笨的體力活。“你是一個被遺棄在一邊的狀態,只能在那邊等著人家去叫你,你還要把耳朵支起來,他喊一聲方子,你要在快速之間用最短的時間把他需要的方子遞給他。”
晚上,工友們躺在大通鋪上,分享村邊的八卦,打撲克。每當這時,他就用被子蒙上頭,假裝睡著了。重復枯燥的生活讓他看不到希望,他時常會想:我這一生難道就這樣了嗎?
頹廢了一個多月后,他給自己找到了一個情緒出口——閱讀。每個不下雨的夜晚,工友們去公園散步,他就在附近的舊書攤看書。每天兩個小時的閱讀時間,被王計兵視作夜里的一節蠟燭,“它是唯一能給你帶來光明的事,感覺每天的盼望和希望就在那。”
但兩個小時不足以看完一本書,第二天再去,書已經被賣出去了。他心里癢癢。
一次雨天,無法出門,他惦記著書里的結局,索性找來紙筆,順著記憶里的情節往下寫了個結尾。久而久之,閱讀和寫作成了排解情緒的方式,“我心情好了,會給他安一個非常好的結局,心情不好了,就給他安一個非常慘的。”
【3】半截圓珠筆
王計兵的衣服內袋里隨時帶著一支筆,收工后的夜晚、撈沙的間隙,靈感來了,他可以隨時隨地寫作。
一次,他脫下新買的黑白條紋襯衫,將黑線當成了紙張的橫線,寫上密密麻麻的句子。
1990年,父親做起撈沙的活,王計兵回到老家幫忙。老家穩定、規律的生活,為他提供了獨立創作的條件。
1991年,他的第一篇微型小說被錄用,編輯楊曉敏給他回信:寫得很好啊,要堅持,很有希望。寡言少語的父母笑了。碰上街坊鄰居,還總忍不住要炫耀一番,“就像考上了大學一樣,他們以為我好像要出人頭地了。”
可是,王計兵還沒看到被刊登的作品,麻煩就先找上了門。原來,這是他根據周圍的環境寫的一篇紀實小說。樣刊被寄到了村里的衛生所,有村民發現自己被當作了小說原型,怒氣沖沖地上門質問,他才知道文章發表了。
陸續刊登了十多篇作品之后,他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為了不被打擾,撈沙之外的時間,他躲進桃林里的小屋。桃樹開花、結果,又變成了枯枝。王計兵日復一日地寫著。
更瘋狂的時候,為了體驗主人公服喪時的心情,他穿上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卻被一位長輩大罵,“她說我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村邊的人也說他“想出名想瘋了”。
越來越多的負面評價涌到家里。父親徹底被激怒。趁著王計兵去撈沙,他拆了小屋,燒了書稿。改了三版、足有20萬字的手稿,變成一堆灰燼,被父親埋進了沙坑。
意識到書稿被燒的瞬間,王計兵覺得萬念俱灰,“感覺我自己建的這座精神上的房子也塌了,整個人間都是暗的。”
他跟父親冷戰了兩個多月,直到準備組建自己的小家。意識到父親的壓力,也為了家庭和諧,他跟父親道歉,承諾對家庭負責,不再寫作。
他確實“安分”了幾個月。直到1993年,他和妻子去到新疆打工。逃離父親的“監控”后,他又忍不住在工作之余開始創作。
妻子不理解。“男人不應該粗枝大葉的,彪悍一點嗎?”最初,她只是表現得不感興趣。時間久了,他愈發感受到妻子的反對,“她發現我在寫東西,會把碗‘哐’地就放在桌子上,有時把鐵盆扔到地上去。”
對于妻子,他是愧疚的。日子過得太窮,家里什么都沒有。“分家就分了80斤麥子,還是借了別人的房子搬出去住的。”
想到妻子的隱忍,他妥協了。他把寫作徹底當作了一件內心的事情,只有妻子不在身邊的時候,才敢偷偷寫上幾句。
圓珠筆被他截成小手指長短,藏在了最深的口袋里,這是他最后的精神寄托。“那時候隨手掏東西,就怕不小心把這支筆從口袋里掏出來。”
他把靈感寫到廢紙上,因為“寫完就可以扔掉”。即便到了后來獨自前往山東打工,王計兵還是不敢保留任何手稿。他曾寫了一首打油詩,26頁,寫了三天,完成的當天,扔進爐灶,一把火燒了。
隱瞞妻子繼續寫作,讓他始終有一種負罪感。即使后來,他們來到昆山,開店、買房,生活漸漸安定了下來,他始終不知道如何開口坦白。
直到2019年,他獲得了微詩大賽“金寫手獎”。他用全部獎金給妻子買了一件外套。看到妻子開心地接過禮物,他長呼了一口氣,“可以跟最親密的人分享自己喜歡的事情,她會為我感到驕傲和開心,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1993年,王計兵與妻子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4】池塘、河流和大海
7月25日,王計兵在微博感謝了老師和朋友,他寫道:如果我低著頭,一定不是因為果實,而是我滿懷恩情深感愧疚……
走紅后,這個皮膚黝黑的男人總是害怕辜負厚愛的人。他給自己的定位,始終是一個有著普通愛好的普通人。“任何一個人,如果你喜歡一件事情,況且你為這件事情做了幾十年,都會有成績的,只是我運氣好,遇到了一個很好的契機。”
他形容自己的詩歌是“吃著網上的百家飯長大的”。
2008年,他剛剛學會通過QQ日志保存自己的作品,一位熟悉詩歌的老鄉無意間看到了他的日記,主動教他斷句、寫詩。在老鄉的幫助下,他陸續在論壇上發布了自己的詩歌,他叫每一位跟帖回復的人“師傅”,逐一感謝大家的點評和指點。
2017年,詩歌逐漸成熟后,他恢復了投稿。隨著作品開始出現在國內外文學期刊,他也在前輩們的引薦下,加入了江蘇省作家協會。今年8月,他的詩歌在蘇州“一畫一詩雙聯展”上展出,預熱的推文中,他的身份是“藝術家拾荒”。
在作品《老花眼睛》里,他寫道:
你們把老花眼鏡/反復摘得又戴上的動作/像極了我反復擦去眼角的淚水/……大地上,太多的河流/都曾經如此努力/最終沒有抵達大海/我的池塘尚且清澈/常以魚蝦為接口,對于故鄉/我還欠一次痛哭失聲
這首誕生在一次詩人聚會上的詩,藏著王計兵對前輩們的感恩。“能被他們邀請去,我是懷著一種感激的心情的,看到他們反復去整理眼鏡,我就想,如果是我做他們的動作,必然是在擦掉被他們感動的喜悅的淚水。”
他將這些為他引路的前輩比作河流,將自己比作池塘,“河流是要奔大海的,但反過來河流奔向池塘的話,是他們在不停地給我修路,讓我能找到奔向大海的方向。”
池塘,是老家門前的池塘。前輩們的眼鏡,也藏著他的遺憾。他始終知道,自己的命運軌跡和在場的前輩們是不一樣的,“既然身為池塘,它就失去了很多奔流的機會。”
在內心深處,王計兵仍然羨慕著這些“有文化”的前輩們。如果能重來,他還是想繼續完成學業,成為讓父母驕傲的“金鳳凰”。但他也相信,是苦難塑造了現在立體的他,“痛苦的另一面,可能就是希望或者說快樂,就看你怎么看待它。”
不送外賣、不寫詩的日子里,他還是一個普通的小老板,日常里充斥著進貨、理貨、算賬、盈虧等字眼。走紅的消息像當年小說刊登的消息一樣,在老家傳開。村民們稱贊他“有本事”。
8月15日,出版社跟他敲定了詩集的初稿。今年春節前,他將出版自己人生的第一本詩集。
池塘終究匯入了河流,奔向大海。
九派新聞記者 陳冬艷
【爆料】請聯系記者微信:linghaojizhe
【來源:九派新聞】
-
世界快訊:皮海洲:大宗交易新規改得好,利于穩定投資者對股票價格的預期
頭條 22-08-23
-
天天熱消息:建業新生活上半年盈利2.89億元,同比增11.4%
頭條 22-08-23
-
要聞速遞:江凌到偃師區調研
頭條 22-08-22
-
全球今日訊!集好吃好用好玩好學于一身,周口解鎖“暢享豫品”新姿勢
頭條 22-08-22
-
全球觀速訊丨河南省濟源市發布暴雨紅色預警
頭條 22-08-22
-
環球熱議:交通運輸部對滴滴出行等11家平臺公司進行提醒式約談
頭條 22-08-22
-
全球視訊!河南省公布有關工業綠色低碳轉型名單,有哪些入選?
頭條 22-08-22
-
天天熱議:河南省緩繳三項社保費政策“全攻略”來了
頭條 22-08-22
-
全球時訊:長城汽車:2030年哈弗品牌將正式停售燃油車
頭條 22-08-22
-
每日熱聞!立方風控鳥·晚報(8月22日)
頭條 22-08-22
-
熱點在線丨河南省財政下達1億元資金,獎補這些企業上市、發債等多元化融資
頭條 22-08-22
-
新消息丨中國建設銀行湖南省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龔蜀雄被查
頭條 22-08-22
-
視焦點訊!佛山創新出臺“菜十三條”,布局萬億預制菜產業新賽道
頭條 22-08-22
-
焦點速讀:工商銀行完成發行400億元二級資本債券
頭條 22-08-22
-
視焦點訊!麥趣爾被罰7315.1萬元!
頭條 22-08-22
-
天天熱訊:拓新藥業擬成立拓新醫藥研究院,為新鄉首批市產業研究院
頭條 22-08-22
-
環球微速訊:拓新藥業上半年凈利潤5405.66萬元,同比增長1.34%
頭條 22-08-22
-
環球信息:財政部擬發行650億元182天貼現國債,8月29日開始計息
頭條 22-08-22
-
天天通訊!最高40萬元!鄭州個人創業擔保貸款額度提高
頭條 22-08-22
-
當前快播:神火股份:上半年凈利45.36億元,同比大增210.07%
頭條 22-08-22
-
環球熱議:華蘭疫苗上半年凈利潤2.98億元,同比扭虧
頭條 22-08-22
-
天天熱資訊!停牌2年多!盈方微重返A股市場 2次臨停 暴漲近500%
頭條 22-08-22
-
環球今亮點!困境中正邦科技:為何1元甩賣子公司
頭條 22-08-22
-
觀焦點:營收增長44.86%!這家上市公司首次獨立披露預制菜類業績
頭條 22-08-22
-
觀熱點:創投日報(8月22日)
頭條 22-08-22
-
當前播報:總投資15億元,信鋼公司煉鐵產能置換項目新1#高爐點火投產
頭條 22-08-22
-
當前信息:河南省地方金融監管局組織召開第3次金融運行分析座談會
頭條 22-08-22
-
每日看點!華蘭生物:上半年凈利5.83億元,疫苗制品銷量大幅增加
頭條 22-08-22
-
觀焦點: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5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
頭條 22-08-22
-
【天天新視野】焦作出臺10條政策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產業發展
頭條 22-08-22
-
世界最新:牽手河南農大!大別山食品產業學院在固始縣揭牌
頭條 22-08-22
-
每日快訊!飛龍股份:收到廣汽埃安60萬能擴供應鏈產能及物料鎖定協議
頭條 22-08-22
-
世界通訊!寧波首套房和二套房房貸利率下調至4.1%和4.9%
頭條 22-08-22
-
環球看熱訊:時隔三個月,LPR再下調
頭條 22-08-22
-
環球信息:最高可獲500萬元獎勵,鶴壁發布支持科技創新發展政策措施等
頭條 22-08-22
-
世界焦點!河南受旱面積1551萬畝,5市啟動水旱災害防御Ⅳ級應急響應
頭條 22-08-22
-
全球新消息丨立方風控鳥·早報(8月22日)
頭條 22-08-22
-
每日消息!河南昨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2例,新增本土無癥狀感染者16例
頭條 22-08-22
-
世界短訊!世界傳感器大會在鄭舉行,資本力量助創新創業大賽項目落地生“金”
頭條 22-08-22
-
世界微資訊!8月份房企已發擬發中期票據超124億元,融資環境有望改善
頭條 22-08-22
-
世界看熱訊:監管部門正在研究將民企債券融資金額納入券商分類評價的加分因素
頭條 22-08-22
-
最新資訊:皮海洲:不妨對現場檢查撤回公司進行重點檢查
頭條 22-08-22
-
天天熱門:身家逾350億富豪遭證監會立案!隆基綠能、連城數控緊急聲明
頭條 22-08-22
-
環球觀速訊丨首次!四川啟動能源保供一級(紅色)應急響應
頭條 22-08-21
-
全球視點!最高抽成70%,水滴籌上熱搜!公司緊急回應
頭條 22-08-21
-
天天速讀:駐馬店公布最新一批人事任免 | 名單
頭條 22-08-21
-
天天實時:科技創新專場再啟!河南省線上常態化銀企對接8月22日舉行
頭條 22-08-21
-
全球微速訊:鄭州數據交易中心揭牌運營!河南18地平臺公司參與出資
頭條 22-08-21
-
當前速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頭條 22-08-21
-
【報資訊】2030年前完成!我國正論證載人登月方案,將建國際月球科研站
頭條 22-08-21
-
全球即時:河南試點推行電動汽車錯避峰充電 低谷時段充電費五折
頭條 22-08-21
-
觀天下!1元甩賣35億子公司!正邦科技這操作是為何?
頭條 22-08-21
-
焦點日報:洛陽鉬業主要指標創歷史新高,上半年盈利41.5億元增長72%
頭條 22-08-21
-
聚焦:朱民:全球高債務、高股市、高泡沫,金融脆弱性目前是很高的
頭條 22-08-21
-
天天日報丨劉瑞軍出任新寧物流總經理,曾供職河南投資集團
頭條 22-08-21

- 環球資訊:14年創作3000余首詩歌的騎手王計2022-08-23
- 【當前獨家】青海海東市平安區新增6名新冠2022-08-23
- 【全球播資訊】8月22日,云南在密切接觸者2022-08-23
- 全球最新:青海海西州新增55名新冠病毒核酸2022-08-23
- 【天天新要聞】油價今日或“五連跌” 95號2022-08-23
- 世界熱資訊!最高40萬元!鄭州個人創業擔保2022-08-23
- 環球微動態丨賣爆了!這種車,出口量翻倍增2022-08-23
- 環球關注:河南省緩繳三項社保費政策“全攻2022-08-23
- 全球球精選!各地科學抗旱 全力以赴保生產2022-08-23
- 世界焦點!“野泳”危險多 路產隊員忙制止2022-08-23
- 全球播報:多部門多地區積極行動——保障生2022-08-23
- 【全球報資訊】有人被毒蛇咬傷!鄭州交警三2022-08-23
- 【新視野】詹姆斯·韋伯望遠鏡拍攝到木星及2022-08-23
- 環球熱文:處暑:秋涼漸起,令人歡喜2022-08-23
- 世界快訊:皮海洲:大宗交易新規改得好,利2022-08-23
- 環球微頭條丨動畫電影《新神榜:楊戩》導演2022-08-23
- 環球信息:澳門特區政府就修改《維護國家安2022-08-23
- 快播:【非凡十年·新鄉篇】魔幻!河南一螺2022-08-23
- 天天快資訊丨河南省財政下達資金1億元支持2022-08-23
- 環球快資訊丨一“港獨”內地刑滿出獄,回港2022-08-23
- 每日簡訊:鄭州寶媽們注意啦!產前檢查費可2022-08-23
- 全球通訊!除黎智英外,亂港“黃媒”壹傳媒2022-08-23
- 報道:速成拿證、擁有金飯碗?警惕你考的是2022-08-23
- 【全球時快訊】劉文祥帶隊考察學習醫養結合2022-08-23
- 環球關注:新華區法院召開安全駕駛工作會議2022-08-23
- 全球資訊:新華區法院組織召開信息化應用培2022-08-23
- 焦點滾動:平頂山市園林綠化中心參加“金秋2022-08-23
- 【天天新要聞】區統計局“三到位”做好資質2022-08-23
- 天天熱消息:建業新生活上半年盈利2.89億元2022-08-23
- 焦點速讀:公公去世后婆婆被子女接走,干凈2022-08-23
精彩推薦
閱讀排行
- 世界熱資訊!最高40萬元!鄭州個人創業擔保貸款額度提高
- 環球關注:河南省緩繳三項社保費政策“全攻略”來了!
- 世界焦點!“野泳”危險多 路產隊員忙制止
- 【全球報資訊】有人被毒蛇咬傷!鄭州交警三支隊民警開道引導護送就醫
- 快播:【非凡十年·新鄉篇】魔幻!河南一螺旋隧道在大山肚里彎彎繞了4.4公里
- 天天快資訊丨河南省財政下達資金1億元支持企業開展多元化融資
- 每日簡訊:鄭州寶媽們注意啦!產前檢查費可網上申報
- 天天資訊:《綠水青山 飛閱河南》南陽篇:楚風漢韻與丹水玉城!宛都為何值得三顧?
- 全球簡訊:“2022新版紅綠燈”實為舊聞,2017年已實施!鄭州交管局稱未接到任何相關通知
- 當前熱議!汛情不再看天臉色可預演 河南省推進“水旱災害防御數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