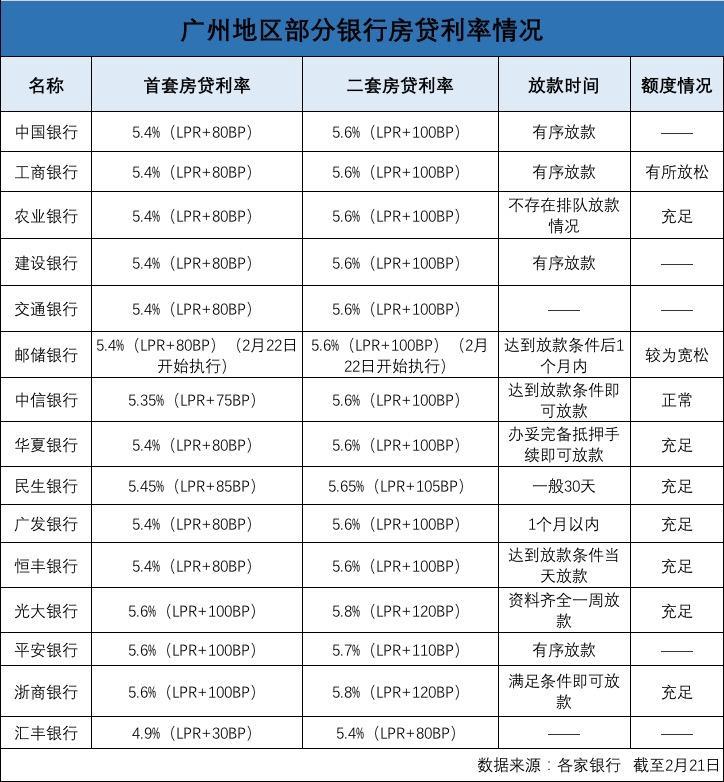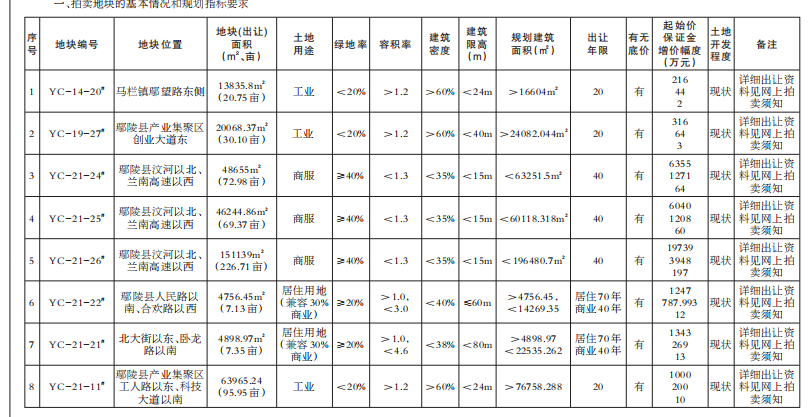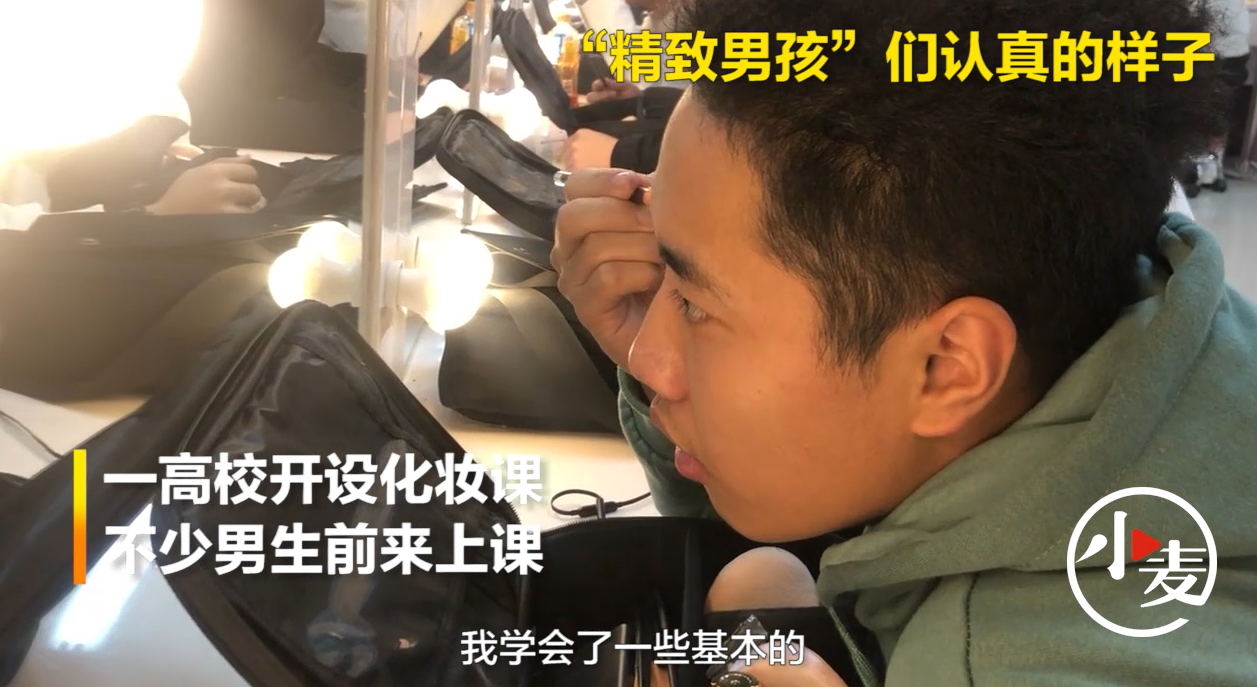周作人的“夜讀抄”,是有意為之的文體。
年初偶然發現,竟然有十來家出版社在印周作人的書。問出版界的朋友,才知道原來周氏著作早在幾年前就已經進入“公版”,無論是誰,不必再征求版權所有者的同意,也不必支付任何費用,就可以拿來出版了。也就是說,知堂老人這次可真的成為“古人”了。
雖然一下子出現多種周氏文集,頗有些蜂擁的感覺,但我相信這些出版者并非著眼于盈利。周氏的讀者無論如何都是“小眾”,而且自恢復出版以后的三十余年,喜歡知堂文字者大都有了一種或多種文集,再印又能有多少人買?所以我的看法是,周作人的“公版”化,只是給出版家們提供一個展示出版理念及構想的機會,當然其前提自是對知堂文字的推重。我有選擇地買了幾種,想看看有什么新的面貌,得到的感覺是,出版者很是動了些心思,力圖別開生面,比如封面的設計以及排版的版式都有新意,特別是有的還加了不僅精美而且恰當的插圖,這是格外讓我心喜的。但在最主要的部分,即文本上,卻看不到下了多少功夫,有些什么改進。我想,這并不是出版者的有意忽視和偷懶,而是他們對知堂著作現有文本的缺陷估計不足所致。
周作人的書自1945年以后,基本處于停止出版的狀態,只是在1950年代之后,在不用“周作人”為署名的前提下出版過幾本關于魯迅的書和翻譯作品,至于他的自編文集,好像從來沒有再版過。所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鐘叔河先生開始較系統地編輯出版周作人自編文集、分類文編,以及止庵先生經過更廣泛地搜集而重新校訂周氏自編文集的時候,他們可憑借參考的資源都很有限,在今天看來,這些出版成果顯得有些倉促和粗糙,也是可以諒解的。鐘先生以多種形式讓周氏作品與讀者見面,止庵先生則為讀者提供一個力求保持原汁原味、本色純正的版本,可以說完成了周氏著作整理的“草創”階段。此外,盡管周氏文本并沒有達到或接近“定本”的水平,但二位在整理校訂的理念上的不同見解,綜合比較來看,卻包含著多方面的正反經驗,這就為后來者的“討論”“修飾”“潤色”提供了可貴的借鑒。
可惜的是,“公版”之后的周氏著作,尚看不到對“草創”階段的突破,卻給人以把那二位校訂者也“公版”化了的感覺。遺憾之余,我忍不住想以讀者身份插幾句嘴,對“公版”之前的周氏文本,包括民國版以及鐘先生、止庵先生的校訂版,聊陳芻蕘之見,以供有志繼武前驅者參考,哪怕招來一些譏笑也不在乎了。
周氏現有的文字我并沒有全部看過,只是讀過其中的大部分。我讀的遍數較多的,只有早期的《看云》《永日》等集,中期的《夜讀抄》以后的十來本而已。所以我的舉例也就限于這個范圍內,而且對每個要談的問題只舉一例,都是“公版”前版本中沒有發現處理的。
一、文本的錯誤
先談文本的錯誤,也就是校勘問題。
(一)周作人本人的筆誤。《秉燭后談》第一篇《自己所能做的》中有如下一段:
這是一件難事情,我怎么敢來動手呢。當初原是不敢,也就是那么逼成的,好像是“八道行成”里的大子,各處彷徨之后往往走到牛角里去。
我的看法是:“大子”之“大”雖然與“太”相通,但還是改為適合
【來源:南方周末客戶端】
-
鄭州市委書記安偉:抓住小切口管住重點人堅決守住防控底線
頭條 22-03-23
-
焦作本輪疫情防控形勢整體可控!
頭條 22-03-23
-
中光學選舉李智超為董事長
頭條 22-03-23
-
立方風控鳥·晚報(3月23日)
頭條 22-03-23
-
已發現的黑匣子經初步判斷為駕駛艙語音記錄器
頭條 22-03-23
-
安圖生物:擬使用不超過3億元自有資金回購公司股份
頭條 22-03-23
-
五年倍增!河南各地力挺企業上市,哪些公司被點名?
頭條 22-03-23
-
明天9點,鄭州二七區開展重點人群核酸檢測
頭條 22-03-23
-
宇通捐贈10輛負壓救護車馳援吉林,助力科學精準防疫
頭條 22-03-23
-
主打“大牌平替”? ?淘特上線“10元店”
頭條 22-03-23
-
國家發改委聲明:并未建立基礎設施REITs有關專家庫
頭條 22-03-23
-
入主太龍藥業剛滿兩個月,鄭州高新投資控股集團擬向其提供12億元財務支持
頭條 22-03-23
-
保障實體經濟發展開門紅,漯河大中型商業銀行為重點項目授信23.96億元
頭條 22-03-23
-
焦作修武新增1例本土無癥狀感染者
頭條 22-03-23
-
央行發布2月份金融市場情況:滬深兩市日均交易量環降逾10%
頭條 22-03-23
-
飛機失事時航路上天氣適航
頭條 22-03-23
-
失事飛機飛行員飛行經歷完備
頭條 22-03-23
-
人民銀行金融科技委會議召開,研究部署2022年重點工作
頭條 22-03-23
-
周口太康: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例、無癥狀感染者1例、初篩陽性人員2人
頭條 22-03-23
-
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例
頭條 22-03-23
-
天邁科技預中標鄭州BRT設備工程項目,總報價3408萬元
頭條 22-03-23
-
騰訊2021年全年凈利潤2248.2億元 同比增長40.65%
頭條 22-03-23
-
3月25日,濮陽將開展第6輪全員核酸檢測
頭條 22-03-23
-
河南開封杞縣新增1例確診,詳情發布
頭條 22-03-23
-
濟源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濟源經濟技術開發區揭牌
頭條 22-03-23
-
周口太康公布2例確診病例活動軌跡
頭條 22-03-23
-
許昌發布14號通告:在主城區和長葛市開展全員核酸檢測
頭條 22-03-23
-
美法院裁定披露!中興通訊復牌H股漲60%,A股漲停
頭條 22-03-23
-
河南新惠建投擬發行5億元私募債獲上交所受理
頭條 22-03-23
-
國家衛健委:不得以沒有核酸檢測結果為由推諉患者
頭條 22-03-23
-
“觀堂機場”不合適?商丘機場如何命名,官方回復了
頭條 22-03-23
-
銀保監會:2021年末國內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余額達15.1萬億元
頭條 22-03-23
-
南陽銀保監分局:推動宛城、臥龍聯社合并組建南陽市農商行
頭條 22-03-23
-
預制菜“熱炒”,河南駛入萬億新賽道 | 豫見預制菜①
頭條 22-03-23
-
洛陽市老城區發現1例新冠肺炎無癥狀感染者
頭條 22-03-23
-
河南省金融局將執法檢查省內282家典當行、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公司
頭條 22-03-23
-
郝以昆任南陽市人社局黨組書記,劉建光任南陽市生態環境局黨組書記
頭條 22-03-23
-
駐馬店發布通告!中心城區全員核酸檢測
頭條 22-03-23
-
哈爾濱市擬廢止實行區域性房地產限售政策
頭條 22-03-23
-
河南自貿區鄭州片區法院發通告:倡導開展網上訴訟
頭條 22-03-23
-
新鄉中新商業保理獲批設立,注冊資本1億元
頭條 22-03-23
-
國家發改委發布氫能產業規劃:探索設立制氫基地、鼓勵氫能企業上市
頭條 22-03-23
-
國家衛健委:昨日本土新增“2591+2346”
頭條 22-03-23
-
比亞迪在深圳成立融資租賃公司,注冊資本10億元
頭條 22-03-23
-
深交所:中興通訊擬披露重大事項,今日開市起臨時停牌
頭條 22-03-23
-
理想汽車:4月1日起 理想ONE售價上調至34.98萬元
頭條 22-03-23
-
旗下第6家上市公司登陸創業板,新希望劉永好的資本版圖里都有誰?
頭條 22-03-23
-
河南昨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6例
頭條 22-03-23
-
通達股份擬中標國家電網1.93億元采購
頭條 22-03-23
-
巴奴總部遷至北京,撈王、七欣天謀求上市,“火鍋第三股”之爭,將花落誰家?
頭條 22-03-23
-
隔夜歐美·3月23日
頭條 22-03-23
-
立方風控鳥·早報(3月23日)
頭條 22-03-23
-
3月22日0時至20時,焦作新增本土無癥狀感染者4例
頭條 22-03-22
-
個轉企、小升規、規改股、股上市、企轉新 洛陽最新支持政策來了!
頭條 22-03-22
-
寶能集團董事長姚振華:已領取法律文書,公司欠了銀行利息
頭條 22-03-22

- “公版”以后的周作人2022-03-23
- 長江評論說熱點|找到一部黑匣子,前方人員2022-03-23
- 李集鎮小開展世界氣象日主題教育活動2022-03-23
- 商橋靳莊小學開展“人人講公開課”教學展示2022-03-23
- 優化營商環境·強化提升科技工作能力作風,2022-03-23
- 淞江許洼小學開展世界氣象日主題教育活動2022-03-23
- 要“闖”的勁頭更要“創”的本領2022-03-23
- 鄭州市委書記安偉:抓住小切口管住重點人堅2022-03-23
- 焦作本輪疫情防控形勢整體可控!2022-03-23
- 大象獨家|中牟縣城連續八天降壓供水:何時2022-03-23
- 廣東省通信管理局依法對3·15晚會曝光的“2022-03-23
- 航空專家解讀:找到駕駛艙話音記錄器有什么2022-03-23
- 茅臺批發價重新跌回2700元/瓶 渠道商:銷2022-03-23
- 藥明康德2021年凈利升逾七成 新增客戶超1660家2022-03-23
- 「星星晚上好」聽見春天的小松鼠2022-03-23
- “天宮課堂”再次開講 孩子們直呼太精彩太2022-03-23
- 奇思妙想巧制作 能工巧匠展風采——鄰水縣2022-03-23
- 四川內江:氣象日“探秘”氣象2022-03-23
- “云端”看鄭州城市職業學院丨探訪鄭州城市2022-03-23
- 黃河路小學開展第62個世界氣象日主題教育活2022-03-23
- 河南財政金融學院:為誰辛苦為誰甜的出彩財2022-03-23
- 河南省周口市氣象臺發布大風藍色預警信號2022-03-23
- 中光學選舉李智超為董事長2022-03-23
- 立方風控鳥·晚報(3月23日)2022-03-23
- 已發現的黑匣子經初步判斷為駕駛艙語音記錄2022-03-23
- 鄭州市政開展汛前演練,提高防汛精細化、高2022-03-23
- 新版核酸檢測指南來啦!你關心的都在這里2022-03-23
- 國家衛生健康委:各級醫療機構不得以任何理2022-03-23
- 各地采取多種措施暢通就醫渠道 保障居民日2022-03-23
- 已發現部分人體組織碎片,黑匣子是艙音記錄2022-03-23
精彩推薦
閱讀排行
- 大象獨家|中牟縣城連續八天降壓供水:何時恢復正常供水? 帶來什么啟示?
- 鄭州市政開展汛前演練,提高防汛精細化、高效化作業水平
- 黑匣子已找到一個,通過它可以獲得哪些訊息?
- 鄭州“以舊換新”拉動家電成“新寵” 消費市場火熱升溫
- 暖心!外地精神障礙女子迷失鄭州 兩地民警接力助其“回家”
- 職在必得|疫情之下就業服務不打烊!鄭州3場大型線上云視頻招聘會即將開啟
- 一部黑匣子已找到!東航客機墜毀事故調查進展:3位飛行員起飛前健康狀況良好
- 一部黑匣子已找到!東航客機墜毀事故調查進展:3位飛行員起飛前健康狀況良好
- 希拉里新冠檢測呈陽性!歐美政壇多人確診,世衛發出新警告
- 完善城市社區“15分鐘健身圈” 2022年河南省群眾體育工作要點發布